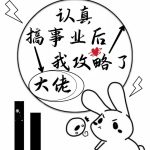萍蹤俠影錄第 45 章 (1)
更新時間:2007-1-12 23:23:22 本章字數:14783
雲蕾的信上只是寥寥數行,叫他諸事辦妥之後,即到東門外的碧羅山上相會。那碧羅山是個名勝之地,靠近瓦刺京城,山上有幾處人家。張丹楓看信之後,心中暗暗納罕:雲蕾從未到過瓦刺京城,人地生疏,怎麽會住到碧羅山上?而且又沒寫明住址,找起來豈不麻煩?又想到她急急遷居,定是逃避也先的偵騎,免不了為她擔憂。
雲蕾既走,張丹楓只好先行回家。也先派來監視的衛士果然全已撤走,澹臺滅明給他開門,兩人相見,自有一番歡喜。澹臺滅明道:“前幾日我們被困在府中,真是悶極了,依我的性兒真想打出去。只是主公卻堅決不許。”張丹楓笑道:“還是不要打的好。我的父親呢?”澹臺滅明道:“主公近日心事重重,你回來了正好。他就在書房內。”
張丹楓輕輕走進書房,只見父親正在支頭默坐若有所思。張丹楓叫了一聲“爹爹”,張宗周道:“嗯,你回來了,我還以為今生難以再見你呢!”眼淚潸然而下。張丹楓道:“不孝兒回來請罪了。”張宗周道:“我聽澹臺将軍說你已到過蘇州了?”張丹楓道:“正是為此請罪,祖先的寶藏和那張地圖我都已發掘來,但卻送給明朝的于謙,讓他幫助朱家天子,打退瓦刺了。”張宗周道:“你的行為,我從澹臺将軍口中亦已約略知道,你此舉對中國有功,但咱們張家卻永無機會再争天下了。”張丹楓默然不語,正想措詞勸說,張宗周又嘆口氣道:“生不願為上柱國,死猶不願作閻羅,閻羅點鬼心常忍,柱國憂民事更多。我經過了這場巨變,雄心壯志,已漸消磨。宰相亦不願做了,做皇帝那更麻煩,你既不願作開國之君,我亦願就此終老異國了。你做的事情我不怪你就是。”張丹楓勸道:“爹,落葉歸根,我還是望你重回故土。”張宗周又嘆了口氣揮揮手道:“你日來勞累,先去歇歇吧,今晚再說。”
晚飯之後,張丹楓與父親漫步園中,但見明月之下,花影扶疏,繡檻雕欄,風光如昔。兩父子倚欄相對,久久無言。張丹楓折下一朵梅花,道:“此處梅花開得比往年更好了。”張宗周道:“是麽?你到過蘇州故宮,那裏的風光如何?”張丹楓道:“那裏已給官家賣出,作為土霸的園林,壁上的碑帖亦已剝落模糊了。”張宗周不勝嘆息。張丹楓道:“爹爹不必擔心,那地方又給孩兒贏回來了。”張宗周道:“怎麽?”張丹楓将當日與九頭獅子賭快活林之事說了一下,張宗周雖然心事滿懷,也給他引得哈哈大笑。張丹楓道:“為兒不孝,但願能侍奉爹爹回去,讓爹爹在園中安享晚年。”張宗周更嘆口氣,神情落漠之極。
張丹楓道:“爹爹正好趁此機會,退出是非之場。”将今早與也先的談話,都告訴了父親,說道:“我已擅作主張替爹爹答允了也先,明兒一早遞上辭呈,不再做這勞什子的瓦刺丞相了。”張宗周道:“這正合我的心意,做了二十多年的丞相我是覺得很疲倦了。當年本就無心做這丞相的。”張丹楓道:“雲無心而出岫,鳥倦飛而知還。爹爹,咱們還是重回家園的好。”張宗周又嘆了口氣,低聲吟道:“雲無心而出岫,鳥倦飛而知還。陶淵明這兩句說得好,歸去來兮,是應該歸去的時候了。”張丹楓喜道:“那麽爹爹明早遞上辭呈,咱們待明朝的使臣到來,兩國議和之後,便行歸國。”張宗周搖了搖頭,忽地沉聲答道:“我所說的歸去,不是你所說的歸國。”張丹楓怔了一怔,道:“怎麽?”張宗周道:“酒闌席散人歸去,富貴繁華一夢空。我在塵世混了六十年,也應歸去了。”聲調蒼涼之極,原來他說的“歸去”指的乃是“撒手歸西”。張丹楓顫聲說道:“爹爹老當益壯,距百年之期尚遠,何為出此不祥之言!”張宗周凄然笑道:“天下無不散之筵席。”張丹楓急道:“江南水軟山溫,正宜回去頤養。”張宗周道:“我還有面目重回江南嗎?昔日楚霸王不肯渡過烏江,他也是不願重見江東父老呀!”矛盾苦悶的心情溢于言表。張丹楓道:“這怎麽能相比呀?”猶待勸說,張宗周擺擺手道:“我意已決,不必多言,丞相之職可辭,祖先的土地是不願重踏了。”張丹楓道:“那麽爹爹是否認為孩兒此次中國之行是做錯了?”張宗周擡首望天,遠處隐隐傳來胡笳之聲,半晌說道:“若然是我年輕四十年,我也會像你這樣幹的。因人成事,大不可靠。現在我已知道想借瓦刺的勢力恢複我們大周的國運,這想法是錯的了。”張丹楓既憂且喜,激動叫道:“爹……”張宗周截着說道:“不必說了。哎,不過我可得提醒你,也先此人,甚是狡猾,還得提防他反複才好。呀,我但願明朝的使臣快快到來。我縱死在瓦刺,也終于忘不了中國呀。聽你所說,于謙是百年難遇的賢臣,但願中國從此國運昌隆,我能見着他派來的人也好。”
這霎時間,張丹楓覺得與父親距離很近又似很遠,感覺到父親心弦的跳動又似覺不能理解,正自凝思,忽見花樹扶疏之處,人影一閃,陡聽得澹臺滅明喝道:“何人如此鬥膽,擅闖相府?”呼的一掌劈去,只聽得“□刺”一聲,一棵花樹,登時斷了,一個灰衣人從花樹叢中直竄出來,澹臺滅明踉踉跄跄地倒退幾步才穩得住身形。張丹楓大吃一驚:誰人有此功力?只聽得那人哈哈笑道:“丹楓,你回來了?”張丹楓定晴一看卻是自己的大師伯董岳,歡喜之極,立刻介紹他與父親相見,陪他回轉客廳。
賓主坐定,董岳啜了口茶,哈哈笑道:“澹臺将軍,你的鐵琵琶掌功夫比以前更俊了。”澹臺滅明也笑道:“你的大力金剛手也更難抵擋了。”張宗周道:“小兒這次在國內得師伯照顧,感激不盡。”董岳道:“敝師弟在瓦刺十年,得你照顧我更感激呢!”又笑道:“丞相之心,我今夜始知,敝師弟果然沒有說錯,好在我沒有魯莽行事。”張丹楓心中一怔想道:“幸而他聽到我爹爹半截的談話,若是二師伯,只怕一來就要動手了。”
張丹楓道:“師伯見到我的師父了嗎?”董岳道:“見着啦。”張宗周道:“謝先生去了多日,事先我毫不知道,擔心得很。他既回到京城,何以不與先生同來?”董岳啜了口茶,沉吟不語。澹臺滅明道:“也先的衛士雖已撤退,難保他不會再派人來暗探。我到前面查夜看看。”話畢即行。張丹楓道:“澹臺将軍也忒多心,他怕我們有什麽話不便在他面前說。”董岳道:“不錯,我所要說的正是他師父的事情。”澹臺滅明的師父上官天野正是玄機逸士的對頭。張丹楓怔了一怔,道:“怎麽?上官這老魔頭不是早已埋名隐世,難道現在又再出山了麽?”
董岳道:“他可沒有出山,但我們卻要給他去拜山了。”張丹楓道:“怎麽?”董岳道:“這老魔頭不知怎麽打聽到我們幾師兄弟都在瓦刺,派人通知了我,要我們進山去谒他。”張丹楓道:“他這是什麽意思?”董岳道:“我也不知道呀。大約是想較考較考我們吧。他是老前輩,既有此命,不可不依的。”張丹楓沉吟說道:“可不知澹臺将軍知道此事否?”董岳面色一沉,道:“他若不說,你休提起。”武林中規矩,兩派的尊長若有相争,門人弟子縱有往來,也應避忌。張丹楓對這些規矩本不放在心中,但見師伯說得如此鄭重,也就不好多所說話。
董岳續道:“三十年前,咱們的師父與上官天野在峨嵋之巅,鬥了三日三夜不分勝負,那時本有三十年之後重會之約。但不久他們兩人就都隐居,一在中原,一在蒙邊,彼此不相往來。我也以為這事說過便算了。哪知今年春初,聽這裏的一位武林朋友說,上官天野仍有意踐約。所以我才趕回去通知你的師祖,當時他老人家不置可否,只說你們先到瓦刺去吧。還不知他會不會來呢。”張丹楓道:“我聽師父說過,師祖所創的雙劍合璧的玄機劍法,就是準備對付這老魔頭的,想來他老人家不願親自出手了。”董岳道:“雙劍合璧的威力我尚未見,三師弟和四師妹雖然聰颍過人,比我強得多,但若說要對付那魔頭,那卻還相差尚遠。”張丹楓深知雙劍合璧的威力,對董岳之言,殊不相信。但不願在師伯面前誇耀自己師父的劍法,亦不出聲。董岳忽道:“丹楓,你的小友呢?”
董岳口中所說的“小友”,當然指的乃是雲蕾。張丹楓心頭一跳,他尚未與父親談過,不願便即提出,當下抛了一個眼色,董岳似解不解,道:“你就不挂念她了嗎?”張宗周道:“楓兒,你既與好友同來,就該請他來見我呀。”張丹楓道:“他有事先走了。”董岳道:“她不是要到唐古拉山南面的峽谷去找母親嗎?”張丹楓心頭又是一跳:原來董岳亦已見着雲蕾了,要不然他不會知道此事。當下歡喜之情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來,他是絕頂聰明的人,當然猜到雲蕾之住到碧羅山乃是董岳的安排了。
張宗周面上現出疑惑的神情,問道:“什麽朋友?”張丹楓道:“一位肝膽照人的朋友。”張宗周道:“既然如此,他日你一定要請他到咱們家裏來。”張丹楓應了一聲,想起雲蕾發誓不願見他父親,心中無限凄酸。
董岳又道:“上官魔頭就在唐古拉山北面的高峰,從南面峽谷愕羅族人聚居之地北行,爬上北面的高峰,大約有三日的路程。适才張大人問起天華,他已經先去了。”張丹楓問道:“上官天野叫你們何時拜山?”董岳道:“日期尚未确定,總在清明之前。天華先走,是我叫他去先會一位武林朋友,必要之時,出來調解的。你的二師伯呢?聽說他也來了,只是天華和我都還沒見着他。”張丹楓道:“他和震三界畢道凡在一起呢。”當下将昨夜發生之事,約略說了一遍。董岳笑道:“潮音的脾氣還是依然如故。好吧,我再逗留幾天,找到他後和他說話。”張丹楓忽道:“那麽,明天我也先走了。”
張宗周愕然道:“楓兒,你剛回來,怎麽又走?”張丹楓道:“師尊有事,弟子服其勞,我的師父既然前往履險,我怎能不追随呢?”張宗周想自己的兒子乃是謝天華一手培養成材的,張丹楓所說的自是正理,當下雖覺黯然,卻也不加阻撓。只是問道:“你那匹照夜獅子馬呢?”張丹楓道:“我那位朋友帶它先走了。”張宗周“哦”了一聲,心道:“他和這位朋友交情确是不比尋常。”心中越發想知道那是何人。
第二日一早董岳和張丹楓向張宗周辭行,張宗周道:“我送你們出去。”攜着兒子的手,緩緩而行,董岳則在澹臺滅明陪伴之下,先到門前相候。張丹楓道:“爹,你回去吧,你還要上朝呢。”張宗周道:“辭呈昨夜我已修好了,不必着忙。從此我無官一身輕,只有盼望你回來了。”張丹楓道:“爹爹不必挂心,我和師父都會回來的。”張宗周道:“只恐你回來這後,又要走了。你回來時,明朝的使臣想亦應當來了。”張丹楓道:“你為什麽不與我們一同回去?”張宗周道:“昨夜早已說過,不必多說了。”張丹楓忽道:“大人可還記得以前那位明朝的使臣雲靖嗎?”
張宗周怔了一怔,張丹楓只覺他的掌心淌汗,微微發抖。過了半晌,張宗周嘆了口氣,說道:“呀,三十年了,三十年前之事還歷歷如在目前,雲使臣是我生平所見的第一條硬漢,我怎會不記得?算起來他回國也有十年了。”張丹楓道:“他剛踏進國門,便被王振假傳聖旨,将他害死了。”張宗周道:“這事情我亦聽說。呀,都是我的罪過。想那時我少年氣盛,恨極明朝的天子,連同效忠明朝的人,我都憎恨,以至令雲靖在冰天雪地的湖邊,牧馬了二十年。他二十年來飲冰嚼雪,對朱家天子始終是丹心一片,他雖然是與我作對,我倒很佩服他的。近年來我一想到這件事情,就覺得難過,這是我生平所作的唯一罪孽。我倒希望将來明朝派來的使臣,也像雲靖一樣,是個鐵铮铮的硬漢。”張丹楓忽道:“聽說雲靖還留下兩個孫兒,一男一女,年歲和我差不多。”張宗周道:“是嗎,但願能見着他們。”張丹楓道:“若然他們有求助于你的地方,你願意嗎?”張宗周道:“你是我所寶貝的兒子,若然要為了他們,舍棄了你,我也情願。”忽又嘆道:“他們若然還在人世長大成人,定知他爺爺當年之事,他們一定将我當作仇人,又怎會向我求助?”張丹楓聽他父親所說的話,出于肺腑,心中大慰,只聽得他父親又道:“你怎麽知道這兩個孩子下落?”張丹楓本想将他與雲蕾之事說知,但一轉念間,卻忍着不說,只道:“聽說他們也跟了明師,學成了一身武藝,雲靖的孫兒好像還在明朝為官呢,我是聽得江湖上的朋友說的。”張宗周喜道:“這樣我就安心了。但願将來明朝派來的使者,就是雲靖的孫兒。”
說話之間,已到了門邊。張丹楓道:“爹爹保重。”和董岳走出後門,只見張宗周淚光瑩然,還倚在門邊凝望。
董岳道:“天華師弟真有耐心遠見,現在我才知道他肯留在你們家中十年的理由。你的父親願暗助中國,看來也先亦興不起什麽波浪了。”
張丹楓道:“師伯,咱們現在上哪兒?”董岳道:“當然是上碧羅山呀,你的小兄弟正在挂念你呢。”張丹楓道:“原來是你老叫她上山去住的。”董岳道:“碧羅山上有我的一位朋友,雲蕾在客店居住,終是不妥,因此我叫她到這位朋友家中暫住。”
兩人腳程甚快,不到一刻就來到了碧羅山。寒冬肅殺,滿山黃葉,但張丹楓心中卻充滿生氣,對着殘冬臘月,卻如看見了明媚的春光。走上半山,只見山坡上一家人家,土牆木門,倒也齊整,門前倚着一個少女,正是雲蕾。張丹楓叫道:“小兄弟,小兄弟,我回來了!”雲蕾淡淡應了一聲,神情甚是冷漠。董岳瞧了他們一眼,搖搖頭道:“你們真是一對冤家。”
張丹楓道:“我和父親談起當年之事,他甚是後悔。”正想告訴雲蕾他的父親是怎樣盼望能見到他們,雲蕾冷冷說道:“我也在後悔呢。”張丹楓道:“後悔什麽?”雲蕾道:“我的爺爺牧馬,我的母親現在給人家放羊,将來若和你一道見着母親,我也不知該怎說好。”張丹楓嘆了口氣。原來雲蕾是覺得和他相好,對不起母親,故此後悔。董岳笑道:“你們這兩個小家夥一見面就唉聲嘆氣,真令我這老頭子莫名其妙,有話進裏面去說。”張丹楓嘆氣道:“我就是赴湯蹈火,也要同你尋着母親。将來不論伯母怎樣責怪我,我也甘受。”雲蕾忽地噗嗤一笑道:“責怪你做什麽?我的母親生平從不責怪人的。別作得那樣可憐相啦。”一笑之下,春意盎然,好像滿天的陰霾都被陽光驅逐了。
董岳的朋友是一位客居蒙古的回族武師,甚是豪爽,接他們進門之後,便自去洗剝昨日獵來的一頭黃羊,給他們下酒。三人坐定,雲蕾道:“三師伯和師父昨天已經走了。”董岳說道:“我已與丹楓說過,我還要在這裏逗留幾天,待尋見你的二師伯和畢道凡之後,再趕到唐古拉山的南高峰赴會。你們尋到了雲蕾的母親後,也要即時趕往,也許咱們老幼兩代,都要合鬥那老魔頭呢!”雲蕾道:“那老魔頭就這樣厲害嗎?”董岳道:“咱們合鬥他,我看也還沒有把握必勝呢。”雲蕾道:“如此說來,豈不是比紫竹林中那位老婆婆還要厲害?”董岳一怔,道:“什麽老婆婆?”雲蕾想起謝天華的話,說是此事除了師祖之外,只有大師伯知道,立即問道:“是一位不肯透露姓名,能夠用竹葉作暗器打人的老婆婆。大師伯,你知道她的來歷嗎?”當下将那日在紫竹林中所遇到的事情一一說與董岳知道。董岳道:“想不到這位老前輩還在人間,尚未忘情當年之事。她既然現身,将來或許也會插手,事情只恐怕更麻煩了。”雲蕾道:“她到底是什麽人?”董岳道:“她和咱們的祖師與那個老魔頭大約都有過一段淵源。只是咱們做小輩的不便談論,将來你自然會知道的。”雲蕾不敢再問,心中更是納悶。
吃過了午飯,方交中午,雲蕾思母情切,催張丹楓收拾,辭別了主人和大師伯,先行動身。那匹照夜獅子馬被雲蕾帶到此地,多日不見主人,見張丹楓走近,便昂首長嘶表示親熱。張丹楓手撫馬頸,笑道:“又用得着你了。”與雲蕾各自跨上寶馬,絕塵而去。
時序已是深冬,愈向北行,朔風愈烈,道路都已被雪掩蓋白茫茫一片,與原野相連,分辨不出。路上絕少行人,張丹楓在馬前揚鞭,高聲放歌道:“但得兩心如白雪,不教半點染塵埃。”雲蕾道:“酸秀才,你再風呀雲呀的一吟,風雪一來,那就更冷得難行了。”張丹楓笑道:“再大的風雪也冷不了我的心。”說話之間,風雪果然來了。
雪片紛飛,朔風怒號,俨如有萬馬奔騰之勢,張丹楓與雲蕾逆風奔馳,衣襟上、馬鞍上盡是雪花,張丹楓索性解開衣紐披襟迎風,揚鞭顧盼,大呼痛快。雲蕾忽道:“咦,你聽,這是風聲還是嘯聲?”張丹楓側耳細辨音響,奇道:“風聲中夾雜着清嘯之聲,還有馬蹄追逐的聲音呢。而且發嘯之人,定是武功高明之士,咱們上前看看。”
張、雲二人放馬飛跑,跑了片刻,只見前面白皚皚的雪地上,有一團黑影滾來滾去,正是兩條大漢在雪地上□打。旁邊還有三騎健馬,馬上騎客是兩個女人和一個身軀魁梧的大漢。
張丹楓道:“似乎是我們認識的朋友。”再放馬走了半裏之地,勒着馬頭,向前一看,原來前面那幾個人正是黑白摩诃和他們的波斯妻子,在雪地上和人□打的是黑摩诃。張丹楓叫了一聲,再看清楚時更奇怪了,和黑摩诃□打的人竟是以前明朝的大內總管康超海!
只見那康超海一身蒙古牧民的服飾,衣裳已被黑摩诃抓裂幾處,更顯得形容憔悴,滿面風塵之色。康超海的氣力遠不及黑摩诃,就在張丹楓勒馬而觀的時候,只見他又被黑摩诃摔了一個筋鬥。張丹楓正自奇怪他們為什麽打架,只見康超海摔了一筋鬥,立刻翻身起來拔出一柄馬刀,狠狠地向黑摩诃劈去,口中罵道:“惡強盜,膽怪在太歲頭上動土,偷我的東西,趕快還來,萬事皆休,否則就一刀将你劈了!”黑摩诃哈哈大笑拔出綠玉寶杖,反手一迎,只聽得當□一聲,火花飛濺,康超海的馬刀碰了一個缺口。黑摩诃笑道:“我還未見過太歲哩,你好好和我說,還有商量,你若想逞強,哼,哼!看是你一刀劈了我,還是我一杖打碎你的狗腿!”話說之間,兩人手底都不放松,瞬息之間已換了三四招。張丹楓十分奇怪,黑白摩诃所做的珠寶買賣,規模之大,世無匹敵,何至于要偷康超海的東西?但看那黑摩诃杖法雖然淩厲,卻是未下殺手,又似乎是有意相讓。
張丹楓知道康超海不是黑摩诃的對手,心道:“此人雖行為卑鄙,但總算和我有一面之雅,不知他何故與黑白摩诃發生糾紛,不如我上前替他們調解吧。”縱馬上前,就在這一瞬間只聽得康超海驚叫一聲,連連後退。
白摩诃駐馬觀鬥,這時也看清楚是張丹楓來了,歡喜之極叫道:“大哥,是張公子來了!”黑摩诃叫道:“張公子來得正好,你把那幾件寶貝給他瞧瞧,看他認得麽?”張丹楓道:“什麽寶貝?”康超海見是張丹楓,心中更是吃驚,但又希望他能幫助自己,急忙叫道:“這兩個強盜,偷盜了我的寶貝,丹楓,你給我主持公道!”
張丹楓問:“你有什麽寶貝?”跳下馬來正想上去勸解,只聽得黑摩诃大笑道:“是啊,你有什麽寶貝?你昨日不矢口否認身有寶物,怎麽現在又說是你的了?”康超海急道:“丹楓,那真是我的寶貝。”張丹楓道:“你哪裏來的寶貝?”白摩诃拿出一個黃布包裹,遞給張丹楓道:“你瞧都在裏面,我看那幾件寶物,來路不正,敢情也是這□偷來的,你給我們瞧瞧,給我們認認這幾件寶物的來歷。”
張丹楓心念一動,這黃布包袱乃是他見過的。明軍在土木堡被圍之時,康超海陣上私逃,到一家農家投宿,恰好被張、雲二人撞見,他背上背的就是這個黃包袱,裏面都是金元寶,當時曾被張丹楓擲于階下,他拾起來就逃跑了。張丹楓心道:“這幾個金元寶怎會放在黑白摩诃心上?”解開包裏,忽見寶光外露,原來除了十幾錠金元寶之外,還有好幾件異寶奇珍!
一件是尺餘長的碧玉珊瑚,通體晶瑩,毫元瑕疵,比雲蕾送給石翠鳳做聘禮的那支珊瑚還要名貴得多。一支是嵌有兩顆“貓兒眼”寶石的頭簪,簪上有“孝欣皇後”幾個籀文篆字。另一樣是鎮紙用的寶石獅子。還有一樣就更名貴了,竟是正統皇帝的龍紋漢玉私章,有“正統皇帝之印”幾個金文刻字,那是僅次于國玺的寶物。另外還有一件商代的古董,一串珍珠項鏈,都在價值連城的大內寶物。
張丹楓冷冷一笑,道:“你哪裏來的這些寶物?”康超海道:“都是皇上歷年賞賜我的。”張丹楓冷笑道:“皇上連他的私章和皇後的頭簪都賞給你嗎?”這時張丹楓已是心中了了料想定是康超海在土木堡私逃之時,把皇帝随身攜帶的珍寶一古腦兒偷了,以至連那“天子之印”以及皇後送與皇帝留念的頭簪都一同盜去。剛從土木堡逃出之時他還不敢包在包袱內,所以當時張丹楓沒有發現。
張丹楓所料不差,那些珍寶都是康超海偷自正統皇帝身上的。那時他以為中國必被瓦刺所滅,天下定将大亂,所以他想偷了這些珍寶,然後隐姓埋名做個富家翁。不料後來也先兵敗新皇登基,康超海做賊心虛,而且他的兩個師叔鐵臂金猿與三花劍又都給張丹楓收服,投了于謙,對他臨陣私逃的行為很是不齒。他生怕師叔追查,又怕新帝知道他偷了正統皇帝的寶物故此把心一橫,逃到蒙古,想在蒙古購置牧場,安享餘生,但那些寶物卻又難以脫手。他又想獻給也先,在瓦刺求一官半職的,正自躊躇不定,卻在路上碰到了黑白摩诃,黑白摩诃做了幾十年的珠寶買賣,一看就知道他身上藏有非常的寶物,對他的來歷甚是懷疑,當時本想向他收買,但康超海矢口否認,黑摩诃一時性起,就在晚上施展空空妙手,将他的寶物以及黃布包袱內的金元寶都盡行偷了。
此時康超海被張丹楓質問,頓時口啞,答不出話來。張丹楓道:“虧你是大內總管,皇帝待你不薄,你在危難之際,棄他而逃已是該死,還敢偷內府的寶物!”黑摩诃大笑道:“果然你也是偷來的。哈,你還是什麽大內總管嗎?好,吃我一杖吧!”天摩杖法一展,有如天風海雨,逼人而來,倏地便下殺手。康超海施展平生本領,使盡吃奶氣力,擋了五招,第六招再也招架不住,馬刀給黑摩诃一杖打飛,杖頭下戳,眼看就要插進他的丹田要穴。張丹楓心有不忍,叫道:“饒他一命,廢了他的武功吧!”黑摩诃一杖下戳,杖頭一偏,便在他的肩頭重重擊了一記,可憐康超海肩上的琵琶骨已被敲碎,所練的金鐘罩也給破了,武功盡廢,只能像常人一樣的了。
張丹楓笑道:“人為財死,鳥為食亡。你今幸而不死,算天大的造化,以後好好做人吧。”康超海得饒了性命,哪裏還敢說話,急急落荒而逃,他從懷有重寶變成身無一文的窮漢,武功又廢,後來只好在牧場替人做工,勞碌一生,郁郁而死。
康超海走後,黑白摩诃重與張丹楓施禮相見,彼此大笑。張丹楓道:“你們從哪裏來?”黑摩诃道:“我剛從印度做了一趟買賣回來,前日才經過唐古拉山。”張丹楓心頭一動道:“那是愕羅族的地方啊,你們有見着酋長嗎?”白摩诃笑道:“我們是買賣人,哪有閑功夫去拜會酋長。倒是另有一些貴人去拜會他了,酋長這幾天正忙着呢。”張丹楓道:“什麽人去拜會他?”黑摩诃道:“說是也先的使者。”張丹楓道:“嗯是也先的使者嗎?”白摩诃道:“聽說也先要收買他,共同對付阿刺,我也是在路上聽得朋友說的,看來瓦刺将有內亂,我們的同行怕戰亂之中會有損失,都準備南下。呀,你的父親是瓦刺宰相,這事情你還不知道嗎?”
張丹楓道:“聽到一點風聲。”眼珠一轉,忽道:“你們将那兩件寶物,圖章和玉簪讓給我吧。家父在瓦刺京城還有點産業,都折價與你交換吧。”黑摩诃大笑道:“不賣不賣!”這兩樣東西,一件是國寶,一件是皇後的東西,張丹楓想贖回來将來送還正統皇帝,聽黑摩诃說不賣,甚是失望。只聽得黑摩诃又笑道:“賣是不賣,但可以送給你,反正是拾來的。不止是那兩件寶物,這黃布包袱裏面的都送與你!”張丹楓道:“什麽,這怎麽行?”黑摩诃又大笑道:“天下就只許你仗義疏財嗎?上次蒙你發還我們輸掉的地下寶藏,這幾件東西你既合用,就一定要請你收下了。”張丹楓眼珠一轉笑道:“好,既然兩位這樣慷慨,那我也就不再客氣,全收下了。我還要請你們兄弟代做一事。”
黑白摩诃平生對誰都不買帳,唯獨佩服張丹楓,當下便說道:“你說吧,天大的事情,我們兄弟也能為你擔當。”張丹楓微笑道:“也不是什麽大事,請你們順便替我帶一封信。”黑摩诃道:“送給誰的?”張丹楓道:“你們此行,大約要經過阿刺知院管轄的西部部落吧?”白摩诃道:“不錯,你是要送信給阿刺嗎?”張丹楓道:“正是。”旅途沒有紙筆,張丹楓就用寶劍在一塊羊皮上刺出字跡,“寫”好了一封信,又取了兩件珍寶,交給黑摩诃道:“就煩你們将這封信和這兩件珍寶,送給阿刺。”黑摩诃随手收下,當下與張丹楓告別,分頭趕路。
雲蕾問道:“大哥,你寫的是什麽信?”張丹楓道:“替愕羅酋長與阿刺相約聯盟的信。”雲蕾詫道:“你怎麽知道愕羅酋長會與阿刺聯盟?”張丹楓笑道:“此事已在我安排之中了,三日之後,你就知道了。”
兩人的坐騎,都是世所罕見的寶馬,雖風雪路滑,每日仍能走三四百裏,三日之後,果然趕到了唐古拉山的山南,兩人放緩繩□,慢慢走進峽谷。
雲蕾放眼舊游之地,童年情事,依稀尚能記憶,雲蕾指點沿途景物,說是在那棵大樹下曾和鄰家的女伴捉迷藏,那個大石邊,曾是她經常坐卧的地方,說着說着,不覺滴下淚來,顯得既是興奮,又是悲涼。張丹楓道:“就要見着媽媽了,還哭什麽?”雲蕾揩了眼淚,道:“我是太高興了。嗯,嗯,你說我好不好和你一同去見她?”張丹楓道:“有什麽不好,怕媽媽笑話你嗎?”雲蕾道:“就怕她知道你是我家的仇人。”張丹楓道:“只要你不把我當作仇人,伯母也一定會将我當作侄子看待。”雲蕾一想母親是個極慈祥的心地善良的女人,如果把和張丹楓的事詳細給她說個清楚,她一定不會怪責,只要母親允許,就不怕哥哥阻撓,想到此處,不覺展眉一笑。張丹楓道:“你笑什麽?”雲蕾道:“就要見着媽媽了,難道還不高興嗎?”
忽而想起媽媽現在正在酋長家做飼馬的傭婦,不知受盡多少委屈辛酸,又不覺悲從中來,笑容頓斂,愁鎖眉端。
張丹楓作了一個鬼臉,笑道:“忽哭忽笑,何苦來哉!”雲蕾給他逗得又是展顏一笑,道:“你也是這樣的啊。”張丹楓道:“那麽咱們是越來越相像了。”雲蕾杏面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