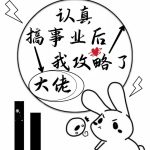萍蹤俠影錄第 23 章 (2)
”久久不答。張風府一笑道:“你不肯說,也就算啦。煩你轉告于他,他可不比金刀寨主,我奉皇命捕他,萬萬不能徇私釋放,看在他也算得是一條好漢,請他遠遠避開,免得大家碰面!好了,為朋友只能做到如此地步你走吧!”
雲蕾飛身上屋,想那張風府行徑,甚是出乎自己意外。想起這樣一位本來具有俠義心腸的熱血男子,卻為皇帝一家一姓賣命,又不覺替他十分不值。陡然又想起自己的爺爺,為了保全大明使節,捱了多少年苦難,卻終于血濺國門,不覺喃喃自語道:“愚忠二字,不知害了多少英雄豪傑!”雲蕾年紀輕輕本不會想到這些千古以來令人困惑的問題--忠于君與忠于國的區別,在封建社會之中,若非有大智慧之人,實是不易分辨清楚。只因她與張丹楓多時相處,不知不覺之間,接受了他的觀念與熏陶,故此敢于蔑視他爺爺那代奉為金科玉律的忠君思想。
雲蕾心內思潮起伏,腳步卻是絲毫不緩,霎時間,出了客店,飛身掠上對面民房,但見鬥轉星橫,已是罩更時分,畢道凡本是在客店外面替她把風,這時雲蕾縱目四顧,卻是杳無人影。雲蕾輕輕擊了三下手掌,畢道凡伏地聽聲的本領十分高明若然他在附近,這三下掌聲,定能聽見,過了一陣,既不聞掌聲回應,亦不見人影出現。雲蕾不覺倒吸一口涼氣心裏着慌。畢道凡到哪裏去了?他是江湖上的大行家、老前輩,斷無受人暗算之理,即說是他見了周山民,也應該等自己出來,一齊回去,于理于情,斷不會不見雲蕾,便悄悄溜走。那麽,畢道凡到底到哪裏去了?
雲蕾四下一望,吸一口氣,施展絕頂輕功,在周圍裏許之地兜了兩個圈子,細心搜索,仍是不見人影,心中想道:“難道是張風府發現了他的蹤跡,預先布下埋伏,将他擒了?不會呀,不會!那張風府一直就在裏面,除了張風府之外,禦林軍的軍官沒一個是畢道凡的對手,即算是張風府,也非鬥個三五百招,不易分出勝負。那又怎會毫無聲響,便被捉去之理?若說不是禦林軍的軍官,另有高手,将他暗算,那麽能不動聲息而能将畢道凡劫去的人,武功實是不可思議。當今之世,也未必有這樣的人。”雲蕾越想越慌,索性直往北門奔去,不須一盞茶的時刻,已到了城外郊區,這是張風府所說,樊忠與周山民等她之處。雲蕾擊掌相呼,登高縱目,但只見星河耿耿,明月在天,寒蟄哀鳴,夜涼如水。休說不見樊忠與周山民二人,整個郊野都像睡去一般,寂靜得令人害怕。
雲蕾又驚又怒,心道:“莫非這是張風府弄的玄虛,我怎能聽他一面之言?敢情他根本就沒有釋放山民大哥?但他卻又何必來騙我來此?”雲蕾滿腹疑團,百思不解,折回身又向城中奔去。
到了客店之外,忽見外面大門虛掩,更是驚詫,索性推門進去,門內院子,本來系有十餘匹馬,這時只見每匹馬都狀如人立,前面兩蹄高高舉起,踢它不動,亦不嘶鳴,在月光之下更顯得怪異無倫,令人毛骨悚然。
雲蕾定一定神,想起這是黑白摩诃制服馬匹的手法,更是大感驚奇:這兩個摩頭,黑白兩道全不買帳,人不犯他亦不犯別人,在青龍峽中,他們雖曾暗助自己一臂之力,卻也只是狂沖疾闖而過,未與官軍作戰,緣何卻要深夜到此,作弄官軍?
雲蕾料知若是黑白摩诃到此,必然尚有下文,飛身上屋,凝神細聽。這客店裏連住宿的官軍在內,總有六七十人,卻竟自聽不出半點聲息,連鼾聲也無,冷森森清寂寂地,簡直有如一座古墳。雲蕾飛身落下內院,想找客店中的夥計,只見房門大開,那曾經給自己帶過路的店小二,熟睡如死,推他捏他,毫無知覺;探他鼻端,卻是有氣;試行推拿又不似被人點穴。再看另外幾間客店夥計自己住的房間,也盡都如此,連那個武功頗有根底的掌櫃,也是癱在床上縮作一團,猶如死去一般。雲蕾心想:“聞道江湖上有一種采花賊常用的迷香,嗅了迷香可以令人熟睡如死,莫非是中了迷香?”盛了一碗冷水,噴那掌櫃,只見他手臂微微抽動了一下,仍是不醒,又不似是中了迷香。
雲蕾縱再膽大,這時也心慌了,跑出外面。但見每間房都是房門大開,住房間的軍官與在大廳上打地鋪的官軍,一個個都是沉沉熟睡。有的手腳伸開,形如一個“大”;有的半靠着牆,雙目緊閉,頭垂至肩,似是正欠身欲起,卻突然中了“妖法”,就此睡去;有的嘴巴張開,面上表情千奇百怪,好似剛剛張口大咱,就突然給人制住。雲蕾吓得冷汗直冒,大叫一聲四面牆壁擋着聲音,回聲嗡嗡作響,雲蕾如置身墳地之中,除了自己,就再也沒有一個生人。
雲蕾定了定神,想那張風府武功極高,那少年軍官亦是一把好手,縱然是黑白摩诃到此,也未必能占上風,怎會一下就給他們弄成這個光景?雲蕾再奔到後院,看那六輛囚車,只見車門鐵檻,全給利器切斷,車中更無半個囚人,黑白摩定是至交友好,他才會将解穴之法教你,你還能狡辯麽?”雲蕾心中生氣,刷刷刷還了三劍,道:“你好無禮,若然我有惡意,何必救你?”那少年軍官道:“那你與他是何關系,快快道來!”雲蕾怒道:“你是我的何人,我要聽你的話?”那少年軍官劈了兩刀,收招說道:“你知道暗算我的乃是誰人?他是瓦刺右丞相張宗周的兒子呀!看你行徑,也是一名俠客,你如今知道了他的來歷,就該助我報仇。”雲蕾心道:“我早已知道了他的來歷,何待你說!”卻好奇問道:“你與他究有何仇?”那少年軍官道:“說來話長,我不止與他有仇,他的一家大小我都要殺個幹淨!再說他既是大奸賊張宗周的兒子,偷入中國,還能懷有什麽好意麽?你既是江湖俠士,你也該與他有仇!”雲蕾打了一個寒噤,在他話中,隐隐聞到羊皮血書那種血腥味道,越看這少年軍官越覺面熟,不覺一陣陣冷意直透心頭,身軀顫抖,牙關打戰。那少年軍官凝神望她道:“你怎麽啦?”
雲蕾強壓制定神答道:“沒什麽。”那少年軍官道:“好啦,咱們打架也打得乏啦,我與你和解了吧。你告訴我你的來歷,我也告訴你我的來歷。”雲蕾道:“我不必你告訴,我知道你是從蒙古來的。”那少年軍官道:“你怎麽知道?”雲蕾道:“你前日偷襲番王,扮那蒙古牧人神情語氣都像極了。”那少年軍官淡淡一笑,道:“是麽?我祖先兩代,本來就是蒙古牧人。”咚的一聲,雲蕾跌倒地上。她的爺爺在蒙古牧馬二十年,她的父親為了營救爺爺,在蒙古隐姓埋名,過的也是牧羊的生活,不錯,他們都曾在蒙古做過牧人,不過不是自願的罷了。
這霎那間,好像有道電流通過全身,雲蕾戰栗之中神經全都麻木了。“他是我的哥哥,不錯,他準是我的哥哥。呵,他真是我的哥哥麽?”雲蕾入京,為的就是探聽哥哥的消息,可是如今遇着了,她心底下卻又希望這人不是她的哥哥。他說起張宗周父子之時,是多麽地恨呵,若然他真是自己的哥哥,知道自己與張丹楓的交情,那又将發生何等樣的事情?雲蕾不願報仇麽?不是,羊皮血書的陰影始終在她心上沒有消除,她喜歡張丹楓,她也恨張丹楓,可是她又不喜歡別人也恨張丹楓,就是這麽古怪的矛盾的心情。
雲蕾咕咚一聲倒在地上。那少年軍官喝道:“你是誰?”錯綜複雜的思想,波浪般的在她心頭翻過,“暫時不要認他!假如他不是哥哥,豈非洩露了自己的身份。何況他又是一個軍官。”雲蕾像在水中沉溺的人,抓着了一根蘆草,抓着了這個可以暫時不認哥哥的“理由”,一躍而起,道:“我是來救周山民的人。”
那少年軍官好生詫異道:“我知道你是來救周山民的人,三更時分,你第一次來時,伏在張大人的屋頂我已經瞧見啦,不過我不喝破罷了。我問的不是這個--”雲蕾道:“你問別的我就不說,你不知道事情有緩急輕重嗎?你瞧,你這裏鬧成這個樣子,虧你還有閑情與我問長問短。我問你,我的周大哥呢?誰到過這裏了?你和張風府的話我也都聽見啦,我知道你也是想救山民大哥的。”
那少年軍官似是霍然醒起,道:“是呵,咱們先進裏面瞧瞧去,張大人不知道為什麽不見出來?”頓了一頓忽道:“其實我與你說的也不是閑話,你真像一個我所要找尋的人,可惜你是男的。呀,這話說來可長,非得一天一晚說不明白,咱們以後再好好的說。”
雲蕾已移動腳步走在前面,不讓他瞧見自己面上的神情,淡淡說道:“裏面鬧成什麽樣子你還不知道嗎?你的兵士全給人弄得像死人啦。你的張大人也不見了。”
那少年軍官“啊呀”一聲便往裏跑,見了裏面的景象,也不禁毛骨悚然,進了張風府的房間,看了兩面牆上所留下的骷髅、猿猴、寶劍等标記,駭然說道:“果然是他們來了!”
雲蕾道:“他們,他們是誰?”那少年軍官道:“黑白摩诃和大內總管康超海的兩個師叔。”雲蕾道:“呵,原來鐵臂金猿龍鎮方與三花劍玄靈子乃是大內總管的師叔,那麽恭喜你們,你們又添多兩個高手了。”那少年軍官甚是不樂道:“你可不知其中利害,若然鐵臂金猿與三花劍知道是我們釋放了周山民,張大人性命難保。”雲蕾道:“周山民真的是已釋放了嗎?”那少年軍官道:“我起先認為張大人不肯釋放,誰知他暗中已有安排。他是叫樊忠悄悄帶人出去的。”雲蕾道:“可是周山民與樊忠現下也不知生死如何。”将自己所遇的奇事說了。那少年軍官嘆了口氣道:“這種意外,誰也料想不到。”雲蕾正想發問,那少年軍官接下去道:“樊忠與周山民偷偷從後門溜走,我在那裏把風巡夜,忽然夜風之中吹進來一股異香我急忙止着呼吸,已吸進一丁點兒,那異香好生厲害,只是吸進少少,就立刻全身酥軟。驀然間一條黑影飛下牆頭,正是張丹楓這個奸賊,我在蒙古認得他。他一出手便用他那邪惡的點穴功夫,我屏住氣不敢呼吸,也不能叫喊,交手五六招,吸進去的迷香,藥性發作,再也支持不住,以至給他點了穴道。”雲蕾心道:“原來如此。怪不得他這樣快便着了張丹楓的道兒呢。可是張丹楓為什麽又要作弄他呢?”那少年軍官接下去說道:“我給他點了穴道,裏面鬧得如何,已是全無知曉。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,外面忽然又飛進兩個人來,一個是熊腰猿面的老者,一個是腰懸長劍的道人,兩人試着給我解穴,卻無法解開,那人罵聲‘膿包’就進去了。其實他們枉為點蒼派的長老,解不開別派的點穴,又何嘗不是膿包?兩人進去之後不一會就聯袂而出,恨恨然大罵黑白摩诃,飛一般地又越牆走了。嗯,他們若遇着這兩個魔頭,可有一場好打。”雲蕾道:“咱們且往青龍峽的方向去尋他們”那少年軍官道了聲好,走出前院,見那些馬匹的怪狀,又好氣又好笑,罵道:“這兩個魔頭連馬賊的陰毒手法也使出來啦,虧我在蒙古多年,對于治馬的功夫還懂一手。”邊說邊替馬推拿拍按,舒散血脈,不久就将兩匹戰馬治好,與雲蕾馳出城外。
這時四野雞鳴,天将近曉,到青龍峽的路上,只見幾條馬蹄痕跡,交錯縱橫。兩人飛馬馳驅,跑了一陣,青龍峽已隐隐在望,到了一條岔路,忽聽得左邊道上,遠遠傳來兵刃交擊之聲,而右邊道上,遠遠又見一人一騎,正在疾跑。那少年軍官道:“我往左邊,你往右邊,分頭探道。”雲蕾縱馬上前,跑了一程,與前面那騎漸漸接近,雲蕾吹了一聲胡哨,那騎馬突然勒住,撥轉馬頭,疾奔而來,馬上的騎客正是禦林軍的指揮有京師第一高手之稱的張風府。
雲蕾舉手招呼,張風府勒住馬頭,疾忙問道:“你那位朋友呢?”雲蕾驀地一怔,說道:“你見着他了麽?我剛剛從你那裏來。”張風府沉吟半晌,道:“那麽此事就真奇怪了,他為什麽引我出來,在這荒野上捉迷藏、兜圈子?”雲蕾問道:“什麽?是他引你出來的?那黑白摩诃呢?”張風府道:“你是說昨日在峽谷之中所遇的那兩個怪物?我沒有見着他們。我送你走後,正在房中靜坐,思考如何應付這事的後果,忽聽得有人輕輕在窗外敲了三下,說道:‘宗兄,我來啦!’此人輕身功夫,真是超凡入聖,連我也聽不出來。我一躍而出,只見他已在屋頂微笑招手。什麽?你還問他是誰?自然就是你那位騎白馬的朋友啦。他叫什麽?嗯,張丹楓。此人行事真是神奇莫測,我實是想與他交納,立刻追上前去。那人晃一晃身,便飛過兩間屋頂,身法之快,無以形容。我猜想他是不便與我在客店之中談話,所以引我出去。我追過了兩條街口,只見兩匹馬在轉角之處等着。張丹楓道聲:‘上馬’,飛身先騎了那匹白馬,我也跳上了另一匹馬,飛馳出城。我以為他定然停馬與我說話,誰知他仍是向前飛跑,我喚他他也不聽,追他又追不上。待不追時,他又放慢馬蹄,在這荒野上引我轉來轉去,真是莫名其妙。”雲蕾道:“現在呢?”張風府道:“他已經過了那邊山坳了。我聽得你在後面呼喚,就不追他啦。嗯,你剛從我那裏來?可有人知覺麽?”雲蕾笑道:“還說什麽知覺?你的人全給黑白摩诃弄死了!”張風府跳起來道:“黑白摩诃有這樣大的膽子?”雲蕾道:“不是真的弄死,但卻與死也相差不多。”将所遇的異狀一一細說。張風府聽得客店中人都沉睡不醒,用冷水噴面也沒效果,沉吟說道:“唔,這果然是黑白摩诃的所為了。西域有一種異香,乃是最厲害的迷藥,名為‘雞鳴五鼓返魂香’,非待天亮,無藥可解。若到天亮,自會醒轉。雖然邪氣得緊,卻是對人無害。看這情形,張丹楓是與黑白摩诃聯手來的,由張丹楓引我走開,再由黑白摩诃施放迷香。咦,我自問與黑白摩诃無冤無仇,與張丹楓也有一段小小的交情,為何他們卻與我開如此這般的一個大玩笑。”
雲蕾道:“我亦是十分不解呀!”再把在客店中所見的奇怪情形,細說下去。張風府聽到鐵臂金猿與三花劍聯袂而來,不覺面色大變。雲蕾道:“他們不是你們的自己人嗎?你害怕怎地?”張風府搖了搖頭,慘笑說道:“你且別問,先說下去吧。”雲蕾一口氣将所遭遇的怪事說完,張風府聽得那少年軍官也着了道兒,不覺苦笑。雲蕾道:“那少年軍官不知何以如此恨他?”雲蕾自是隐着張丹楓的身份不說。張風府沉吟半晌道:“看那張丹楓器宇軒昂,當不會是個壞人。雲統領何以恨他,這事我倒要問個明白。”雲蕾聽得一個“雲”字,不覺面色慘白,搖搖欲墜。張風府急忙伸手相扶道:“你怎麽啦?”雲蕾撥馬避開,定了心神,道:“沒什麽。那軍官叫什麽名字啊?”張風府道:“姓雲名喚千裏,你問他作甚?”千裏二字合成一個“重”字,雲重正是幼年就與雲蕾分手的哥哥。雲蕾此時更無疑惑,心中又是歡喜又是驚惶。歡喜者乃是兄妹畢竟重逢,驚惶者乃是他與張丹楓勢成水火。只聽得張風府又道:“你們可是相識的麽?”雲蕾道:“他像我幼年的一位朋友。嗯,他是什麽時候回來的?”張風府道:“回來?咦,你也知道他是從蒙古回來的麽?他到禦林軍中未滿一月,我是錦衣衛指揮兼禦林軍都統,正好是他上司相處時日雖淺,卻是意氣相投。據他說,他的祖先兩代,都是留在瓦刺國的漢人,飽受欺淩,所以逃回。他立志要做一個将軍,好他日領兵去滅瓦刺。所以先在禦林軍混個出身,準備考今年特開的武科,若然中了武科狀元,那就可遂他的平生之願了。”雲蕾不覺嘆口氣道:“他想做官報仇,只恐未必能遂心願。張大人,你休怿我直說,真正抵禦胡虜的可不是大明朝廷。”張風府默然不語,半晌說道:“你所見也未必盡然,我朝中盡有赤膽忠心誓禦外侮的大臣,閣老于謙,就是萬人景仰的正直臣子。”雲蕾不熟悉朝廷之事,當下亦不與他分辨。
張風府見雲蕾甚是關心那個少年軍官,好生奇怪,正想再問,忽聽得一聲馬嘶,張丹楓那騎白馬又奔了回來。張風府叫道:“喂,你弄的究竟是什麽玄虛?你的好友在此,不要再捉迷藏了吧!”張丹楓白馬如飛,霎忽即到,先向張風府道聲:“得罪!”再向雲蕾說道:“你好!”雲蕾扶着馬鞍,冷冷說道:“不勞牽挂。”
張風府見二人神情,并不象是好友,奇異莫名。可是急于知道他的用意,不暇多管閑事,便率直問道:“張兄,你我也算得上有段交情,何以你與黑白摩诃到我住所搗亂?”張丹楓仰天大笑,吟道:“一片苦心君不識,人前枉自說恩仇。我問你,你可知道什麽人來查探你麽?”張風府臉色一變,道:“你也知道了麽?鐵臂金猿龍鎮方和三花劍玄靈子也來了。”張丹楓道:“可不正是,他們因何而來,難道你還不明白麽?”
鐵臂金猿與三花劍乃是當今大內總管康超海的師叔,這康超海乃點蒼派領袖淩霄子的首徒,兩臂有千斤神力,外家功夫登峰造極,只因他長處宮內,保衛皇帝,所以在江湖之上,聲名反而不顯。他不忿張風府有京師第一高手之稱,曾三次約他比試,每次都輸了一招,口中雖說佩報,心中卻是不忿,所以暗地裏常排擠他,張風府亦是明白。康超海的職位比張風府高,張風府對他甚有顧忌。張丹楓一番說話,說得張風府面色大變,喃喃說道:“莫非康超海将他的兩個師叔請來,暗中想加害于我?”張丹楓笑道:“何須暗中加害,現下你就有痛腳捏在他的手裏。”張風府道:“什麽?”張丹楓道:“鐵臂金猿與三花劍本來不是為你出京,可是卻剛好撞上你的事情。你欲知個中原委麽?”張風府道:“請道其詳。”張丹楓道:“黑白摩诃買了一宗賊贓,乃是京中某親王的傳家之寶:一對碧玉獅子,單那鑲嵌獅子眼睛的那兩對明珠,就價值連城,這事情鬧得大了,康超海自知不是黑白摩诃的對手,所以請兩個師叔出山相助查緝。他們料定黑白摩诃必是逃回西域,是故一路北來。卻剛好你也在這一帶,所以順便就将你監視上啦。無巧不巧,你捉了金刀寨主的兒子,你還未知道他的身分,康總管已是得人告知,周山民的身價可更在那對玉獅子之上,能擒至京,便是大功一件。康總管立刻将追贓之事抛過一邊,一面飛書傳報,一面請他的兩個師叔連夜趕到你那裏提人。周山民前腳出門,他們後腳趕至。”張風府驚呼道:“若然他們知道我将周山民釋放,這事可是滅族之禍。”張丹楓笑道:“他們已被我用計引開,這事他們永不知道。”張風府道:“呵,你原來是用黑白摩诃為餌,引開他們。你竟然能指使這兩個魔頭,佩服,佩服!可是你們在客店之中的那場搗亂,卻又是為何?”張丹楓道:“他們雖不知道周山民是你釋放,但失了重犯,這罪名可也不小哇!張大人宗兄,你熟讀兵書,當知黃蓋的苦肉之計。”張風府恍然大悟,在馬上抱拳施禮道:“多謝大恩,沒齒不忘!”雲蕾尚未明白,禁不住問道:“你們弄的究竟是甚玄虛?”張風府道:“他們打開囚車,放走囚犯,我自然難逃罪責,可是來的若是極厲害的敵人,我們人人受制,那就說我已盡力而為,只因力所不敵,并無佯敗私放的嫌疑,那罪名就減輕了。”張丹楓道:“不但如此,以你的聲名,本來戰敗已是有罪,但若來襲的敵人,把本事比你更高的人都打敗了,那麽康總管也就不好意思降罪你啦。”張風府道:“那就是說你們準備給鐵臂金猿與三花劍一點厲害嘗嘗了,你們誰能打敗他們麽?”張丹楓笑道:“你且細聽!”
只聽得山坳那邊一陣陣高呼酣鬥之聲,似是正向這邊追殺過來,張丹楓道:“還有三裏路程,張大人,我還要送你一點薄禮。”張丹楓手中提着一個紅布包裹,圓鼓鼓的好象內中藏着一個西瓜。張風府接了過來,打開一看,內中藏的竟是一個人頭,張風府面色大變,手起一刀,向張丹楓迎面劈去,嘴中罵道:“你為何殺了我的二弟,這難道也是苦肉之計嗎?”雲蕾在旁,也看得清清楚楚,這正是與張風府、樊忠合稱京師三大高手,內廷衛士貫仲的頭顱。
張風府這一刀乃是在急怒攻心之下劈出,威勢猛捷無倫。只見張丹楓大叫一聲:“哇哇不得了!”整個身軀,飛了起來!正是:
又見張郎施妙計,一場大禍弭無形。
欲知後事如何?且看下回分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