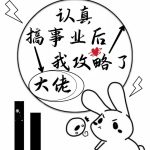萍蹤俠影錄第 13 章 (2)
壁摸索,敲敲打打,笑道:“這裏面還有密室。”在地上取起一根石條,抵着牆角一處凹入之處左右旋轉,過了一會石壁忽然分開,現出一道暗門,原來這種帝王公侯的“地下宮殿”,都是這種建築。石門內側與門外相對稱的地方,有凸起部分,用以承托一根特別制造的石條,名叫“自來石”,用作頂門之用。自來石兩端略寬,刻有蓮瓣,中間略窄,在石門關閉之時,自來石上端頂着門內凸起部分,下端嵌入門外地面上一個凹槽內,若是不明其中道理,任憑外面的人如何用力推那石門也推不開。
暗門開啓,張丹楓扶雲蕾入內,忽見裏面寶光閃耀,有玉幾石案,堆滿古玩金寶。張丹楓一皺眉頭,随手一掃,将金寶古玩全部撥落地上,踢到牆角,道:“別讓這些勞什子阻礙地方。”扶雲蕾在玉幾上坐下,笑道:“這古玉溫涼,倒是大可助你吸去身上的熱毒。”輕輕拉起雲蕾右手,自食指尖端,沿食指的拇指側上緣,通過第一、第二掌骨之間,上入腕上拇指後兩筋之間的凹陷處,輕輕推拿,這是陽明經脈循行部位,走肩峰前緣,與諸陽經相會于柱骨的大椎之上,再向下入缺盆,聯絡肺髒。推拿了一陣,雲蕾只覺微微有一股熱氣直透心頭,再過一陣,說也奇怪,心頭燥漸減,遍體生涼。張丹楓放開了手,道:“你的陽明經脈已是貫通,你自己運氣行血,固本培原吧,明日我再替你打通太陽經脈。”
密室裏有美酒內脯,想是那黑白摩诃所留,張丹楓飲酒嚼肉,忽而朗聲吟道:“少婦城南欲斷腸,征人薊北空回首,邊風飄飄那可度,絕域蒼茫更何有?殺氣三時作陣雲,寒聲一夜傳刁鬥。呀呀,帝王蝼蟻同塵土,世上何人能不朽!”歌聲如笑如哭,似是厭恨那終古不息的幹戈,故借歌詞發出無窮的感慨。
雲蕾正在用功,聽那歌聲陡地心頭一震,不覺沖口說道:“戰争自是悲慘之事,但若被蒙古人打了進來,那麽不論男女老幼,卻都該執幹戈以衛社稷。為國家立大功之人,亦可算是不朽之人了。”張丹楓身子微微發抖,一杯酒潑在地上,回過頭道:“小兄弟,趕快用功,不要說話。我一時忘形,痛飲狂歌,驚動你了。”雲蕾吐了口氣,小嘴兒一撅,執拗地問道:“大歌,你說,我的話到底是對與不對?”張丹楓喝了口酒,道:“對極,對極!其實想打仗的人都不是老百姓,若然豪傑之士都不想稱王稱帝争奪江山,豈不甚好?嗯,小兄弟,咱們別再談論了,你快快專心用功吧。”雲蕾思潮一起無法平伏,心中想道:“這大哥為人甚好,何以一談到蒙古與中國之間的戰事,就似甚為痛苦,這是何因?這是何因?……”疑問叢生不能平息。張丹楓緩緩走到她的面前,道:“小兄弟,我本欲待你傷好之後,與你說個痛快,但看你的樣子,似乎不說個明白,就不能靜下心思用功。”雲蕾低聲道:“是呀。”張丹楓道:“但你的傷勢,實在不宜分神說話。我們之間所要說的,又不是一時半刻可以說得明白,這樣吧,你現在靜心用功,到吃晚飯之時,我給你說一個故事,你每日都要吃一次晚飯,照我估度,你三日之後可好,那麽我就每日給你說一個故事。到了第四日,你全好了,咱們再彼此将身世來歷傾吐出來。小兄弟,你若然是不聽話,我就連故事也不說與你聽,哪,你現在不許問了,快快用功。”
張丹楓的眼光似乎含有一種強制的力量,雲蕾只覺有這樣一種感覺:自己還是小孩子的時候,母親每晚在她床邊唱蒙古的催眠小曲,那充滿柔情的眼光,令人永不能忘。張丹楓這時的眼光就叫她想起母親。可是兩人的眼光有相同卻又有不同。她又想起爺爺每次教訓她時那種嚴厲的眼光,張丹楓的眼光又叫她想起爺爺。這既是慈愛的又是嚴厲的眼光,有一種令人不可抵抗的力量,雲蕾不知不覺如受催眠,心情慢慢地平靜下去了,不久就專心一致地用起功來。
這古墓是倚山崦建,墓中密室的一邊,就是石山的峭壁,光滑如鏡,屋頂上端有有兩個石罅,恰恰可作透氣通風之用,對着墓門的石壁嵌有一面小銅鏡,這密室構造各甚是特別,室內的人可以透過銅鏡,看到外面,外面的人卻看不進來。這時陽光從石罅透進室內,看地上的日影,似乎已過午時,外面忽然傳來一陣聲響,似乎有人挖門,外面的墓門,在昨晚波斯婦人帶張、雲二人進來之時,已被損壞了下面的突起的蓮瓣,沒有“自來石”頂住,外面的人挖松了泥土之後一推就推開了。那銅鏡的色澤和牆壁的色澤一樣,雲蕾仔細辨認,那影在銅鏡上的模糊人影竟然似是一個熟悉的少女。雲蕾心中一動,急用衣袖揩抹銅境,一瞧清楚,險險叫出聲來,這個少女不是別人正是轟天雷石英的女兒石翠鳳。
只見石翠鳳摸摸索索走了進來,邊走邊叫道:“雲相公,雲相公!”雲蕾心中暗笑:“我們還只是半夜‘夫妻’,她對我倒思念得緊。”墓中光線暗淡,石翠鳳走近通道,走上大廳“嚓”的一聲,燃起火石,見殿上插有十二枝牛油巨燭,正合心意,一一點燃,把大廳照耀得明如白晝。密室內暗嵌的銅鏡照出石翠鳳的面容,令雲蕾吃了一驚:數日不見,她竟然憔悴如斯!
銅境內映出石翠鳳往來察看,忽然蹲在地上,“哇”的一聲哭了出來。原來她在地上發現了一灘鮮血,那本是白摩诃中劍所流的血她卻以為是雲蕾的。黑白摩诃是她父親的老主顧,她自是深知這個摩頭的厲害,心中想道:“雲相公被黑白摩诃所傷,只怕不死也成殘廢。”故此哀哀痛哭。
雲蕾見她哭得傷心,十分不忍,跳了起來,想開門出去,張丹楓一把将她按住道:“不管外面如何,你都不要出聲,”抵着她的掌心,又助她動氣行血。
只見石翠鳳哭了一陣,從懷裏掏出一枝珊瑚,放在案上,那正是雲蕾送給她的聘物,她摩挲再四,哭了一陣,又哀哀叫道:“弟弟,弟弟,我好苦命呵!”雲蕾心中連聲叫道:“姐姐,我還未死,我還未死呢!”可是石翠鳳哪能聽見,她又哭又叫,忽地拔出佩刀,揚空虛斫一刀,叫道:“蕾弟,不管那兩個魔頭如何厲害,我一定要爹爹替你報仇!”反身走出,走了幾步,忽然又蹲了下來,在地上拾起兩片金環,那是黑摩诃頭上的束發金環,早上激戰之時,被張丹楓削斷了的。石翠鳳喃喃說道:“咦,難道那兩魔頭沒有騙我?”将兩片金環翻來覆去地看,怔怔出神。
原來那晚雲蕾走後,石翠鳳乘快馬追趕,在路上碰見黑白摩诃,向他們打聽有沒有見過像雲蕾這樣看青俊俏的小夥子,黑白摩诃問了雲蕾的形狀,冷笑一聲,問道:“他是你的什麽人?”石翠鳳依實說了,黑摩诃“哼”了一聲道:“好侄女,你配的好夫婿,功夫真不錯呀!”石翠鳳驚道:“你老如何知道?”黑摩诃冷冷說道:“他替你贏了一大筆珠寶,我在此地所有的都輸給他了。轟天雷有這樣的好女婿,自樂得金盤洗手不必幹啦。”石翠鳳一驚,道:“什麽,他居然敢和你老動手了?”黑摩诃怒目相視,以為石翠鳳是存心氣他,不理不答,與白摩诃一怒而去。
石翠鳳知道黑白摩诃秘密的藏身墓窟,慌忙趕到,她做夢也想不到雲蕾居然會打敗黑白摩诃,此際發現了黑摩诃被削斷的金環,兀是将信将疑,心中想道:“以黑白摩诃那樣大的本領,絕無輸給雲蕾的道理。但以黑白摩诃那樣大的名頭,亦似乎不會說謊,這是怎麽回事,難道是另有別人傷了蕾弟麽?”她還以為地上所流的是雲蕾的鮮血。正在思疑不定,忽聽得外面一聲馬嘶,只見一個少年牽着一匹紅馬,走入墓道,這匹馬正是雲蕾的紅鬃戰馬。雲蕾一見,又幾乎嚷出聲來!
這少年不是別人,正是金刀寨主周健的兒子周山民,他奉了父親之命,入關來辦一件事情,并探聽雲蕾的蹤跡。經過此地,見了雲蕾的紅馬,那紅鬃戰馬,本是周山民的坐騎,因此把他帶入墓穴。
那紅馬歡躍嘶鳴,似是向舊主人示意,雲蕾就在裏面,周山民正在暗暗稱奇,陡然想起黑白摩诃愛住古墓的怪僻行徑,不覺吓出一身冷汗。進了墓門,見大廳上燈火輝煌,杳無一人更是吃驚,正想出聲呼喚,忽見一個披頭散發的女子,在牆角暗處突然躍出,一刀就劈過來。原來石翠鳳哭了半天,已是神志昏亂,見了雲蕾的紅鬃戰馬,竟認定周山民就是暗算雲蕾之人。
石翠鳳這一刀來勢甚猛,周山民吓了一跳,急急閃開,石翠鳳第二刀又斜裏劈到,周山民拔出腰刀,将她隔開,只見石翠鳳狀若瘋狂,第三刀、第四刀連環劈至,周山民叫道:“喂我與你無冤無仇,何故施行暗襲?”
石翠鳳連劈四刀,猛然想道:“這□本事與我相若,怎能是雲蕾對手?”再劈兩刀,揚聲問道:“兀你這□,快說實話這紅鬃戰馬,你是從何處得來?”
周山民哈哈一笑,霍地跳開,手撫紅馬,說道:“這紅鬃戰馬,本來就是我的坐騎,你問它作甚?”那紅馬挨着周山民□擦,狀極親熱,似是證實周山民所說非假。
石翠鳳“哼”了一聲,鋼刀一晃,劈到中途,見此情狀忽又停住,心中想道:“這紅鬃戰馬,性烈非常,怎肯如此聽他說話?”
只見周山民目光四射,忽然停在當中石案之上,一眼瞥見那枝珊瑚,面色立變,倏地跳去,伸手便拿,石翠鳳鋼刀一晃隔在當中,怒聲斥道:“你做什麽?”周山民道:“咦,你做什麽?”石翠鳳冷笑道:“莫非這珊瑚也是你的麽?”周山民又是哈哈一笑昂頭說道:“實不相瞞,這珊瑚正是在下的!”聲調一變,厲聲問道:“兀你這婆娘,快說實話,你這珊瑚是偷來的還是劫來的?”須知這枝珊瑚實是周健送與雲蕾,雲蕾再送與翠鳳的,周山民見了珊瑚,不由得心生疑慮。
石翠鳳大怒跳起,霍的一刀又劈過去,周山民還了一刀,絕不客氣,勁力奇大,石翠鳳的刀幾給震飛,急用蹑雲步法身形一轉,繞到周山民背後,周山民反手一刀,沒有掃中,兩人登時又打起來。
雲蕾在密室中見兩人打鬥甚烈,極為着急,竟不能安心運氣吐納,張丹楓雙掌抵着雲蕾掌心,低聲說道:“別急,他們二人誰也勝不了誰。那男子是你熟識的麽?”雲蕾點了點頭,忽想起張丹楓撕毀日月雙旗之事,瞪他一眼,弄得張丹楓莫名其妙。
周山民與石翠鳳鬥了三五十招,一個勝在刀沉力勁,一個勝在身靈步捷,果是不分勝負,石翠鳳斫了一刀,忽然揚聲喝道:“你說珊瑚是你的,你有什麽記號?”
周山民哈哈一笑,說道:“諒你這劫賊也不知道,你看那珊瑚的第三葉葉底,是不是刻有一個周字?”石翠鳳日來睹物思人,把玩那枝珊瑚何止數十百遍,那“周”字她早已發現,心中一直懷疑,何以雲蕾送給她的聘禮,卻刻上別人的姓氏,見周山民如此一說,忽地恍然大悟,抽刀跳出圈子問道:“喂你是不是雲蕾的義兄?”周山民不覺一怔,也抽刀躍過一邊,道:“你既知我是雲蕾的義兄,何以不知這珊瑚乃是我送與她的?”
石翠鳳想起那晚洞房情事,雲蕾老是把“他”的“義兄”說個不休,不覺盯了山民一眼,只覺山民雖不及雲蕾清秀,剛健威武,卻更有男子氣慨。這時他也正眼光光地盯着自己,不覺臉上一紅,“呸”了一聲,她想到那晚情事,心中實是惱怒雲蕾。周山民道:“憑你這個女賊,就想強占我的東西麽?”石翠鳳大怒說道:“什麽你的東西?這珊瑚是雲蕾送給我的聘禮,不看你是雲蕾義兄的面上,我就一刀把你劈了!”
周山民頓時愕在當場,片刻說道:“什麽聘禮?雲蕾是你何人?”石翠鳳道:“他是我的丈夫,我也不怕說與你聽。”周山民突然哈哈大笑,忽而想道:“雲蕾喬裝打扮單身上京,身世之秘,實是不能給人知道,所以連這個女子也給她瞞過,我不應揭穿她的面目。”笑聲倏地停住,問道:“姑娘,你姓甚名誰?是幾時與雲蕾成的親?”
石翠鳳這一氣非同小可,手按刀柄,睜目說道:“轟天雷石英是我的父親,三日之前我們成親,怎麽樣?石英的女兒配不上你的義弟麽?”
周山民頗出意外,手撫刀柄,施了一禮,道:“弟嫂休怒我實是無輕視之意。石老英雄可好?”石翠鳳氣呼呼地答道:“好!”周山民道:“你們成親三日,他都在黑石莊麽?”周山民不好意思問及洞房情狀,故此旁敲側擊,石翠鳳道:“他當晚追一白馬賊人,至今不知消息。”
周山民大吃一驚,他正是為那“白馬賊人”而來,便道:“是不是一個書生模樣的白馬少年?”石翠鳳道:“我未見過他的面貌。”周山民道:“他的白馬神駿非常,是也不是?”石翠鳳道:“不錯,我們黑石莊最好的馬都追它不上。”周山民道:“你快領我去見石老英雄,傳綠林箭捉捕這□。哎喲,雲蕾只恐被這奸賊害了!”
密室內外,雲蕾與石翠鳳同吃一驚,只聽得石翠鳳問道:“什麽奸賊?我只以為他是一個黑吃黑的劫寶賊人,但我爹爹卻說他不是,我問過爹爹他是誰,爹爹又不肯說,言談之間,爹爹反而好像對他甚為尊敬,這究竟是怎麽一回事?”
周山民冷冷一笑,道:“他嗎--”墓門外影子一晃,忽然又走進一人,頓時把周山民的說話打斷。雲蕾一見,又吃一驚,這人乃是那晚在古寺外與她動過手的胡賊,澹臺滅明的徒弟!只見周山民一躍而起,揮刀便斬,大聲罵道:“大膽胡兒偷入中國,意欲何為!”原來澹臺滅明與他的徒弟都曾領兵打過周健,周山民曾與他交過手。
澹臺滅明的徒弟名叫哈達萊,一進墓門便大聲叫道:“張相公!”驀見周山民一刀劈到,急拔雙鈎抵擋,叮當一聲,把周山民的金刀格過一邊,喝道:“是你把張相公害了麽?”周山民道:“連你也要碎屍萬段!”揮刀力斫,哈達萊雙鈎一立縱橫揮舞,招數變化無窮,将周山民殺得只有招架之功,毫無還刀之力。
石翠鳳眼看周山民就要落敗,心道:“這個大伯雖無禮,我卻定要助他。”抽出佩刀,上前夾攻。石翠鳳身法輕盈,在哈達萊之上,氣力雖然不勝,但有周山民擋住,兩人長短互補兩柄單刀夭矯如龍,立刻将哈達萊的兇焰壓住,着着反擊。
哈達萊發一聲嘯,雙鈎斜飛,将兩口單刀迫開,明是進攻實是敗走,只見他奮力一擊立刻抽身急走,周山民哪裏肯舍,與石翠鳳急急跟蹤追擊,片刻之後,三人的聲音都去得遠了。
密室之中,雲蕾思疑不定,擡頭一看,只見張丹楓含笑望着自己,似乎是在說道:“你瞧我是個奸賊麽?”雲蕾對周健父子本是十分相信,若非這幾日與張丹楓同行,聽到周山民那一聲“奸賊”,只怕就要拔劍刺他。這時心中好生矛盾,周山民斷斷不會胡亂誣人,而張丹楓又絕對不似一個“奸賊”,同行幾日,她對張丹楓已是由憎厭而變為喜歡,甚至于可以說是有幾分崇拜他了,心中想道:“他從蒙古回來,只怕是像我爺爺那樣逃走出的漢族志士,所以蒙古要捕他回去,而周山民也誤會他是個奸細了。”自猜自想,心中釋然,忽然微微一笑,低聲說道:大哥,我相信你!“
張丹楓臉色舒展,現出無限欣悅之情,低聲說道:”賢弟,你是我生平第一知己。好好用功吧,今晚我給你說第一個故事。“開了密室,走出外面将墓門重又關上,又搬過兩根石條頂住,非有千斤氣力,再也難開。
雲蕾專心用功,導氣運行,甚覺舒服,過了許久,屋頂石隙,已無陽光射進,知是黃昏,黑白摩诃在密室之中留有食糧,張丹楓生火煮了一鍋稀粥,把肉脯、凍雞之類煮熱,服侍雲蕾食粥,雲蕾甚是感激,只見張丹楓溫柔一笑,道:“你好些了,但還不宜多說話,你只聽我,不要多問,我現在就給你說第一個故事。三個故事說完之後,然後我再詳細将我的來歷說與你知。”正是:
身世離奇難以說,花明柳暗費疑猜。
欲知後事如何?請看下回分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