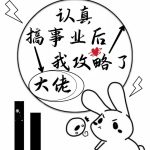萍蹤俠影錄第 2 章 (2)
通紅,謝天華伸手在他胸口一揉,雲靖“哇”的一聲吐出一口濃痰,大叫道:“氣死我也!”顫巍巍地坐了起來。謝天華知道他是憤火中燒,痰塞喉頭,身上并無受到其他傷損,這才放下了心。正待善言開解,忽聽得潮音和尚呱呱大聲,橫拖禪杖,從山坳外疾跑回來。
謝天華又吃了一驚,連忙問道:“師兄,你怎麽啦?”潮音和尚憤然說道:“三弟,我丢盡師門的面子啦!我今生不把澹臺滅明痛打三百禪杖,難消此恨!”謝天華知道師兄是個急性的人,按他坐下,讓他喝了口水,說道:“二師兄,有話慢慢說,憑着咱們四個兄弟,就算是上官老魔頭親自到臨,這仇也可以報,何況澹臺滅明呢?”潮音和尚咕嘟嘟地喝了一大口水,氣憤地續道:“我只道這□要對雲大人暗施毒手,心急趕回,叵耐那兩個小賊,死纏不放,若是平日,這兩個小賊我真還不放在心上。無奈我接連兩場惡鬥,氣力不加,和他們邊走邊鬥,進進退退,竟然趕不回來,鬥了一二百招,我一急連走險招,剛剛搶了上風,不料澹臺滅明這□又回來了。我以為他已将雲大人害了,破口大罵。那□雙鈎一搭,将我的禪杖拉過一邊,突然勁力一松,暗施詭計,将我跌了一跤。這還不算,還打了我一個耳光,罵我是‘莽和尚’,說我‘胡說八道,亂嚼舌頭,打個耳光,聊作薄懲’雲雲。罵完之後,便帶了兩個小賊,揚長而去。我們闖蕩江湖幾十年,幾曾受過如此欺侮,你說氣不氣人?”停了一停,目光注地上,忽然又嚷起來道:“這是怎麽回事?他和你交了手沒有?雲大人好端端的沒事,這地上卻有着三個這樣趣致的錦囊?”
潮音和尚一邊說一邊把三道錦囊拾了起來,啧啧贊賞道:“上面還鄉有駱駝呢。咦,這不是蒙古人的刺繡嗎?這、這是誰的?”雲靖勃然怒道:“臭鞑子的臭東西,把它撕成粉碎,抛到污泥裏去!”潮音愕然一望,用力便撕,忽然手腕一痛,三道錦囊,都給謝天華搶去。潮音和尚詫道:“師弟,你這是……”謝天華道:“雲大人看一看也不礙事,你便看它說的什麽。若然真是胡說八道,那時再撕,也還不遲!”
謝天會心中十分疑惑:這澹臺滅明武功高強之極,他既然不欲加害雲靖,那麽所為的又是何來?難道真是想“救人”不成?但他何以又在蒙古為官,二十年來助那張宗周折磨雲靖?再說雁門關已經在望,踏入了中國地方,還有誰會加害雲靖?這不是騙人的鬼話嗎?但若說他萬裏遠來,為的就是說這番鬼話,卻又是絕無此理。何況他雖然傲岸,卻又似乎手下留情,要不然師兄怎能逃得性命,這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了!
不說謝天華心裏沉吟,且說雲靖接過錦囊,恨恨一瞥,只見第一道錦囊上寫着“即開”二字,雲靖氣呼呼地一把撕開,抽出裏面的信箋,上面寫道:“此時速回蒙古,尚可無事,澹臺将軍留駐左雲,可以接應。”雲靖看完之後,随手一撕,抛在地上.
謝天華見他白須顫抖,面色焦黃,不敢動問。雲靖看着那撕碎的紙片一片片飄落污泥,憤然說道:“什麽錦囊妙計,還不是那番鬼話!”拿起第二道錦囊,只見上面寫道:“離雁門關七裏之地開拆。”雲靖道:“偏不聽你的話。”用力一撕,裏面又露出一張信箋寫道:“時機已迫,此際雁門關當有人接你,先行領隊者苦非周健總兵,你當立即快馬飛逃,留謝天華與潮音斷後,或許尚能保全首領。”雁門關叫兵周健和雲靖乃是同鄉好友,一人習文,一人習武,是同科中的文武進士。雲澄此次救父,得他暗助甚多,實行救父計劃之前,又已派人飛騎報知周總兵,叫他轉告朝廷,一路行蹤,都派有人暗中聯系的。雲靖想道:“周健見我到來,豈有不來迎接之理?我節比蘇武,異域歸來,大明天子即算不立像記功,也當重用。胡兒妄圖離間,真真豈有此理!”随手一撕,又把信箋撕成粉碎。
謝天華旁肯偷窺,一瞥之下,見信箋上有自己的名字,怪而問道:“上面說的什麽?”雲靖鄙屑說道:“還不是鬼話連篇。不過奸賊也真厲害,他們好像已預知你們二人深入胡邊,前來救我。不知何以又無防?”謝天華眉頭一皺,低首沉吟,疑惑更甚。雲靖随手又拿起第三道錦囊,正要撕開,忽又放下了,謝天華一見,不覺叫出聲來。
那第三道錦囊上寫着:“此函交謝天華開拆。”雲靖冷冷地看了謝天華一眼,心起疑雲。謝天華久歷江湖,人甚精細,見此以,微微一笑,說道:“奸賊詭計多端,雲大人你拆開看看,他說什麽?”雲靖略一遲疑,把錦囊慢慢拆開,抽出信箋來,緩緩讀道:“此際雲大人當已被捕,錦囊之內,尚有蠟丸一個,你密藏此丸,切不可開,急速入京,面見于謙,參劾王振,雲大人性命能否保全,全在此一舉矣。”雲靖“哼”了一聲,怒不可遏,信手一撕,又把信箋撕成粉碎,罵道:“危言聳聽,胡說八道!我雲某是個大大的忠臣,豈有被捕之理?”又把錦囊往地下一擲。謝天華一縱身接過錦囊,果然在其中掬出一顆蠟丸,藏在身上。雲靖面色一變,謝天華道:“且藏着這玩意兒,也占不了什麽地方,玩玩也好。”雲靖“哼”了一聲,微愠說道:“這是給你的東西,你要藏便藏着吧。我雲靖與奸賊不共戴天,縱然真是碎屍萬段,也不要他來相救。”
驢車趁着月色,在夜間趕路,雁門關外,邊境守夜的明兵角聲,已隐隐可聞。雲靖精神一振,雖奔波長路,一晚未睡,卻是毫無倦意。翹首長空,縱聲吟道:“喜有餘生歸故土,雄關分隔別華夷。我雲某明日當可重整衣冠,手持使節,禮拜明君了。”謝天華道:“大人孤忠,百世不可一見,而今天子,封官敘爵,也不足言酬。”雲靖微微笑道:“這是臣子份內之事,豈望朝廷酬報。”停了一停,忽然問道:“我去國之時,尚是永樂十年,而今已經歷二十載,換了三朝,朝廷之事,全無所知,不知如今是誰當政?”謝天華道:“是王振當權。”雲靖想起第三道錦囊中的說話,沖口說道:“那麽天佑我朝,這王振一定是個大大的忠臣,只有那個于謙想必是奸臣了。”
潮音和尚正縱馬上來,傍着驢車,聽了雲靖言語,忽然把碗口大的禪杖往地下一頓,大聲說道:“大人錯了,這王振是個大大的奸臣,若然他要撞在灑家手上,也要教他吃我一頓禪杖!”雲靖愕然說道:“什麽,他是奸臣?不會,不會吧!若然他是奸臣,胡兒何以又要唆使什麽于謙出頭,去參劾他。”謝天華道:“大人有所不知,這王振的确是個奸宦。”雲靖詫道:“什麽,他是個太監嗎?”謝天華道:“正是。聽說此人原先在故鄉蔚州讀過書,下過考場,做過縣官,後來犯了罪,本當充軍,适逢皇帝下诏‘有子者亦準淨身入內’,王振遂鑽進了皇宮。後來奉派侍奉太子,亦即當今皇上讀書,至先帝歸天,太子即位,王振遂得任司禮太監,管理內外奏章,于是遂勾結朝臣,擅作威福,巧立名目,苛征暴斂,雖然不過三年,百姓已是恨之入骨。大人此次回去,也要當心。”雲靖聽了,不覺愕然,亦是狐疑滿腹。
謝天華續言道:“那于謙官居兵部侍郎,聽說倒是為官清正。”雲靖聽了,默然不語,心中想道:“這兩人乃是江湖上的莽夫,所言不足深信,待我回朝之後,再親自看個明白。”又想道:“兵法有雲:虛者實之,實者虛之,縱然這兩人所說是實,也定是張宗周布下的圈套,故意叫我相信他的話,其中必定藏有陰謀。”
驢車上雲蕾睡得正酣,雲靖望着她蘋果般的臉兒,天真無邪,可愛之極。想到他年雲蕾長大之後,也要遠赴胡邊,沖霜冒雪,替自己報仇,不覺嘆了口氣。但瞬息之間,二十年來嚼雪飲冰,捱饑抵冷種種苦難,又在心頭泛起,恨火燒心,蓋過了為雲蕾憐惜之念。眼望夜空,心潮浪湧,過了些時,不覺迷迷糊糊地和衣睡了。
一覺醒來,已是第二日清晨,雁門關上的旌旗,已經可以清楚望見。潮音和尚道:“這是七裏鋪,離雁門關只有七裏路了。前面就是雁門關外檢查行旅的衛所了。”雲靖跳了起來,揭開簾幕,問道:“周總後俨了沒有?”潮音和尚道:“天華師弟已入內通報去了。不曾聽說周總兵要來。”雲靖怔了怔,忽而失笑,自言自語道:“我也給那個鬼錦囊弄錯了。周總兵怎會知道我今日到來?通報之後,他自然會來迎我。”便吩咐停下驢車,在衛所之前等待。衛卒們在城牆內張望着,并無任何動靜。
且說謝天華為人,膽大心細,先入雁門關通報,便是他的主意。雁門關的總兵周健,謝天華也曾見過幾面,深知這位邊關守将,不但是雲靖的同鄉舊友,而且俠骨英風,與江湖豪傑胸襟無二。七裏路程轉瞬即到,雁門關上了無異狀,仍是由前幾次帶引自己的旗牌官接待入內,謝天華心頭一寬,暗笑道:“澹臺滅明故布疑陣,裝神弄鬼,連我也受他迷惑了。只要周總兵仍鎮守此關,有誰敢加害雲靖?”
帳中坐定,旗牌官獻上茶來,說道:“總兵大人就要出來了,謝俠士你歇息會兒。”謝天華喝了香茶,卸下護身袍甲,正在等待,忽覺頭昏眼花,叫聲“不好!”連忙拔劍,那旗牌官已搶先一步,将他寶劍奪去,帳外呼呼兩聲,抛進了兩條絆馬索,将他絆倒。
謝天華內功深湛,雖然中了暗算,尚未昏迷,掙紮欲起,卻是渾身無力,而且昏昏思睡,眼皮漸漸睜不開來。謝天華默運玄功,與睡魔相抗,迷迷糊糊之中,似已被人扛起,不久又聽得關門下鎖之聲,似是已給人關在一間黑沉沉的屋子裏了。
那碗茶中溶有極厲害的蒙汗藥,尋常之人,淺嘗即倒,謝天華練過易筋洗髓的功夫,運氣相抗,使自己保持着心頭的一片清醒。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,房門呀呀推開,一個人探頭進來,謝天華定睛一瞧,正是雁門關的總兵周健。
謝天華托地跳起,使盡氣力,呼的一掌橫掃,向他腦門劈去。周健橫肱一架,叫道:“是我!”謝天華氣力未複,給他一架,跄跄踉踉地倒退數步,一頭撞在牆上,怒叫道:“好,知人知面不知心,總兵大人,你用的下三流的暗算手段,用得真到家呀!”周健邁前兩步,把他手腕一拿,低聲叫道:“事情已急,快服下解藥,我與你救雲大人去。你的寶劍我替你拿回來了,快呀!”謝天華驚愕之極,叫道:“什麽?你、你是什麽用意?”黑室之中,但見周健雙眸炯炯,別具威嚴,低聲說道:“我周健是何等之人,你還不知道嗎?此際事機已急,有話慢說,你快随我出去。”謝天華不由得張開了嘴,吞下了周健塞來的藥丸。謝天華心頭本就清醒,吞下解藥,睡意全消了,接過周健遞來的寶劍,躍出門外。
雁門關外號角長鳴,只見先前那名用蒙汗藥偷施暗算的旗牌官攔上前來,高聲叫道:“周大人,你可得三思而行,別要自誤前程!”周健一聲不響,突然一躍而起,揮刀一斬,将那旗牌官斬為兩截,奪了兩騎快馬,與謝天華奔出轅門,關外官兵,無人敢擋。
周健威風凜凜,殺氣騰騰,在馬背上揚鞭指道:“他們正在七裏鋪外□殺,你我抄小路去!”一撥馬頭,從山邊小徑馳去,大路上車馬奔馳,許多人高聲呼喊,叫周總兵回來。周健毫不理睬。
且說雲靖在七裏鋪的衛所外等了許久,正自生氣,忽見路上塵頭大起,十幾騎快馬飛奔而來,不一刻衛所打開,戍守衛所的官長披挂出迎,高聲請進。雲靖看得清楚,那從雁門關來迎接的十幾騎快馬,其中并無周健在內,心中十分不快,但仍是怡然自若,手持使節,步入邊關。
衛所內設好座位,只見十六名禦林軍分成兩隊,分列在階下,堂上兩名欽差,冠帶出迎。雲靖頓時歡喜起來,心中想:“原來是聖天子特降天恩,念我二十年守節,竟然派欽差到邊關迎接來了。”正說得句“雲某何功,敢勞欽差遠接”,堂上的欽差,面孔一端,忽然間高聲喝叱道:“叛臣雲靖,跪下接旨!”
雲靖這一驚非同小可,手持使節,顫聲辯道:“雲某出使異國,二十年來牧馬胡邊,尚存此節,自問無罪,不敢接此诏書!”話猶未了,已給兩名禦林軍按倒地上。只聽得其中一名欽差,展開招書,高聲讀道:
“罪臣雲靖,先帝寄以腹心,遣使瓦刺,乃不感恩圖報,反□顏事仇,忘其父母之國。今日私自歸來,圖謀內應,罪無可恕,本應明正典刑,姑念其是前朝舊臣,恩開法外,準其仰藥自裁,全屍收殓。欽此。”
雲靖魂不附體,只見一名禦林軍捧着一只銀瓶,內中藥水殷紅,高聲叫道:“罪臣雲靖還不謝恩領旨麽?”
雲靖只覺腦門上轟的一聲,又驚又氣又急又怒,忽然一手抓過銀瓶,尖聲叫道:“給诏書我看,我不信這是真的!”欽差冷笑一聲,喝道:“好大的膽子,诏書是你看得的嗎?”話猶未了,只聽得轟天價的一聲巨響,兩扇半掩的大門憑空飛了起來,一個莽和尚提着一碗口般粗大的禪杖,潑風似的打将入來,高聲喝道:“管它真的假的,都打死了再說!”十六名禦林軍上前抵敵,哪能抵敵得住?只見他指東打西,指南打北,禪杖所到之處,有如開山裂石,只要挨着一點,便不死即傷。
那兩個欽差吓得面青唇白,腿都軟了。那和尚一路打到堂上,左後一抻,兀鷹抓雞似地提起了一名欽差,罵道:“雲大人舍命逃回,你們還要将他弄死,是何道理?”“蔔”的一禪杖,敲在他的頭上,甩手一摔,腦漿塗地,死于階下。另一名欽差吓得神智昏亂,兀自叫道:“反了,反了!冒犯欽差,該當何罪?”那和尚放聲大笑,又一把将他抓了起來,罵他道:“兀這□鳥,欽差值得我少錢一斤?”禪杖往地上一插,硬生生地将他撕成兩片。禦林軍紛紛逃出,吹起號角,衛所內屍橫遍地,只剩下了和尚和雲靖二人。
雲靖目瞪口呆,恍如在一場惡夢之中,不知目前所發生的種種事情是真是假,定了定神,見潮音和尚朝他走來,猛然叫道:“把那诏書給我。”
潮音和尚咧嘴冷笑,道:“還有什麽鳥诏書,快快随我走吧!”雲靖盤膝一坐,一字一句,斬釘截鐵地說道:“把那诏書給我!”潮音和尚橫他一眼,在幾案上抓起诏書,摔給他:“好,快看!快看!”對他如此固執,萬分不解。
雲靖展開诏書,一瞥之下,面如死灰,那诏書上的玉玺,與诏書的格式紙質,都是真的。雲靖還記得以前成祖奪位,曾在內監手上搶奪玉玺,那內監将玉玺摔下天階,缺了一角,後來叫巧匠重補,紋理兩樣,而今細辨這诏書上的玉玺,正是如此,絕對假冒不來。
潮音和尚叫道:“看夠了沒有?”雲靖眼睛直視,聽而不聞。這一瞬間,二十年來在胡邊所受的苦難,閃電般地在腦海之中掠過。然而這一切苦難,比起而今的痛苦,簡直算不了什麽。須知雲靖能夠支撐二十年,全在忠君一念,滿以為逃回之後,朝廷必定升官敘爵,表揚功績,哪知皇帝竟是親下诏書,将他處死。正如對一個人崇拜信仰到了極點,期望極深,忽而發現那個人就是要害死自己的人,這一種絕望的痛苦心情,世界上還有什麽可超過?
潮音和尚叫了兩聲,不見答應,心中大異。忽見雲靖緩緩站了起來,将那一根伴随他在冰天雪裏二十年的使節,用力一拗,“啪”的一聲,折為兩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