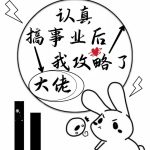萍蹤俠影錄第 26 章 (2)
明的面張風府又不願将這個原因說出,拒絕路家兄弟的挑戰,當下慨然說道:“既然兩位有此雅興,張某只好奉陪,咱們彼此印證武功,點到為止,勝敗不論。”路家兄弟笑道:“這個自然,是勝是敗,都樂得一個哈哈。”兩人左右一分,各自抽出盾牌利劍。
雲蕾好不煩躁,心道:“好端端的又比什麽武?”可是自己乃是外人,不便勸阻,只好在旁觀看。只見張風府抽出緬刀道聲:“進招吧!”路明道:“張大人先請!”緬刀揚空一閃用“五虎斷門刀”中的“截”字訣,橫刀截斬路明的手腕。只聽得“當”的一聲,路亮的盾牌倏然伸出,迎着刀鋒便砸,張風府早知他有此一招,刀碰鐵牌,順勢彈起,青光閃處,一招“紅霞奪目”,刀鋒直取路亮的咽喉。路明利劍一揮,搶攻硬削張風府的臂膊,張風府回刀一隔,将他的攻勢一舉化開。
路明一看,盾牌與刀鋒相接之處,竟給戳了一個小指頭般粗大的凹陷,不禁駭然,心道:“我只道他已疲累不堪,卻還有如此氣力。”不敢怠慢,将盾牌舞得呼呼風響,掩護兄弟進攻。這路家六十三路混元牌法,厲害之處全在這面盾牌,砸、壓、按、劈,善守能攻,确有幾路獨門手法。至于那口劍不過全在盾牌掩護之下,施行攻襲。不過因它有盾牌掩護,可以全采攻勢,威力無形中就增加了一倍。
若在平時,這兩兄弟自然不是張風府的對手,可是如今張風府氣力尚未恢複,武功打了折扣,他又想以快刀斬亂麻的手法速戰速決,不到一盞茶的時刻,已搶攻的三五十招,哪知路家兄弟配合得十分之好,帶攻帶守竟令張風府不能各個擊破。三五十招一過,張風府氣力不加,路亮盾牌一挺,一個“迅雷貫頂”,向張風府當頭打下。張風府知他牌沉力猛,這一下子少說也有七八百斤力量,若然自己氣力充沛的話,這七八百斤之力,自然算不了什麽,可是在氣衰力竭之時,卻不敢硬架硬接了。哪知張風府這麽一閃,路亮的鐵牌如影随形,追着緬刀硬碰硬壓,立刻把張風府迫得處在下風,路明的利劍,攻勢驟盛,如毒蛇吐舌般随着鐵牌進退一伸一縮,劍劍不離張風府的要害。
雲蕾尚未曉知內中含有危機,看得十分納罕,心中想道:“這是怎麽回事?看來可并不像只是印證武功啊!”忽見路亮霍地塌腰虎伏,一個旋轉,盾牌翹起,一招“橫掃千軍”,攔腰便劈,張風府急忙一個“龍形飛步”,從鐵牌之下掠出,一甩腕,還了一招“螳□展臂”,刀鋒下斬敵人雙足,哪知真個是“螳螂捕蟬,黃雀在後”,招數剛剛使出,路明卻突然從側面一劍刺來!
雲蕾驚叫一聲,手指急彈,将一枚“梅花蝴蝶镖”飛出,路明這一劍刺出,滿拟在張風府的身上搠個透明的窟窿,不料“铮”的一聲,劍尖突給梅花蝴蝶镖打中,歪過一邊,未看清暗器來路,急忙按劍一閃,正待喝問,雲蕾也正想躍出,忽見那澹臺滅明突然飛身躍起,叫道:“我還要再打一場,你們兩位既然要留此伴我,為了酬謝盛情,我就舍命陪陪君子吧!張大人,請你退下!”話未說完,人已飛到,他運氣九轉,氣力已充沛如常。只見他左手一拿,右掌一劈,呼的一掌,竟把路亮的鐵牌震得飛上半空,路明的那口利劍也給他劈手奪過,拗折兩段,路家兄弟驚得呆了。說時遲,那時快,澹臺滅明一手一個,倏地将路明、路亮舉了起來,喝聲:“去!”一個旋風急舞,将二人擲出數丈開外,痛得他們狂嗥慘叫,眼前金星亂舞,暈了過去。
澹臺滅明仰天狂笑,說道:“有生以來,今日打得最痛快了!”向張風府點頭一禮,又向雲蕾打了個招呼,道:“我還要打那老頭兒去,少陪了!”邁開大步,走出張家的練武場。
張風府慌忙上前察看路家兄弟的傷勢,只見路明給摔斷了兩根筋骨,路亮跌斷了兩只門牙,澹臺滅明這一摔用的乃是巧勁,只令他們受了外傷,并不妨及性命。張風府給他們敷上金創止能之藥,兩人唧唧哼哼,一跛一拐的自行回去。
張風府嘆了口氣道:“呀,真是料想不到!”雲蕾問道:“什麽料想不到?”張風府道:“我一向不受王振的籠絡,這兩人乃是王振的心腹武士,看來剛才之事乃是王振的指使,有意加害于我了。”雲蕾想不到京師的武士也是各有派系,互相忌刻,但她另有心事,不願多問。只聽得張風府問道:“嗯,你那位朋友張丹楓張相公呢?”雲蕾面上一紅,道:“在青龍峽之後,我們就分手了。”張風府道:“可惜可惜!要不然,你們二人在此,雙劍合璧,定可将澹臺滅明打敗。這三日來他連勝十場,幸有那怪老頭兒挫折了他一下銳氣,但各自受傷,也不過是打成平手。呀,這次可真是丢了我們京師武士的面子了。”雲蕾見他甚是難過,笑道:“你也并沒有敗給澹臺滅明呀!”張風府道:“幸是那怪老頭兒來得及時,要不然不說落敗,連性命恐怕也丢了!這怪老頭兒也不知是怎樣進來的?這麽多武士,竟沒有一人發現,給他擠進了場中。”頓了一頓,又道:“這澹臺滅明也怪,剛才若不是他那麽一插手,恐怕我也難逃暗算。嗯,說起來我還要多謝你那枚梅花蝴蝶镖呢!”
雲蕾迫不及待,無心多說閑話,張風府話聲一歇,她立即問道:“張大人,我今次入京,實是有一事要求你相助。”張風府道:“請說。”雲蕾道:“你部下那位姓雲的少年軍官,求你請他來與我相見可好?”張風府眨眨眼睛,甚是奇怪道:“你入京就是為了此事麽?”
雲蕾道:“不錯,就是為了此事。”張風府道:“你與雲統領有何親故,怎麽我從未聽他提過。”雲蕾道:“彼此同姓是以渴欲一識。”張風府心道:“天下同姓者甚多,這理由可說不通。”雲蕾又道:“若張大人有事,請将雲統領的地址告知,我自己去找他也是一樣。”張風府忽然微微一笑,說道:“這事情且慢慢商量,請進內邊去說。”雲蕾心道:“這事情有甚商量,告訴我不就完了。”但自己乃是客人,不便多問。
張風府帶雲蕾走出練武場所,讓雲蕾進客廳坐定,叫家人泡了壺好茶,道聲:“得罪,我進去換換衣服。”經過與澹臺滅明那場惡鬥,張風府身穿的青色箭衣竟給澹臺滅明用“鐵指銅琵”的功夫撕裂了好幾處,而且衣上沾滿塵沙,連頭發也是一片黃色。雲蕾心中有事,未說之前,還不覺得,既說之後,仔細一瞧,見張風府就像經過沙漠、長途跋涉的旅人一樣,衣裳破碎,滿面風塵之色,果然十分難看,不禁笑道:“那澹臺滅明真是厲害,好在是你,還經受得住。”
張風府進去換衣,雲蕾等得好不心急,好不容易,才等到張風府出來急忙問道:“張大人,那雲統領究竟住在何處?”張風府慢條斯理地整整衣服,坐了下來,啜了口茶,這才含笑說道:“雲統領可難見到啦!”雲蕾吓了一跳問道:“什麽?他遇了什麽意外麽?”一種對親人關切的感情,自然流露,張風府瞧在眼裏,又微微笑道:“是有意外,不過這‘意外’乃是好事,他給皇上看中,已調到內廷當侍衛去了,輕易不能出宮,所以說難于相見。”雲蕾大急,道:“你也不能喚他出來嗎?”張風府道:“現在他已不歸我所統屬,自然不能。”雲蕾道:“這卻如何是好?”張風府道:“你若想見他,半月之後或者可有機會。”雲蕾道:“願聞其故。”張風府道:“半月之後,今年武舉特科開試,千裏兄已報了名,想他武藝超群娴熟兵法,當有武狀元之望。若他中了武狀元,皇上自然賞以軍職,賜邸另居,不必再在宮內當侍衛了。”
雲蕾好生失望,當下便想告辭。張風府卻留着她談話,追憶當日在青龍峽之事,又誇獎了一頓張丹楓,說是全憑他的智計,金刀周健的兒子和自己才得以兩保全。雲蕾每聽他提起張丹楓心中就是“蔔”的一跳,張風府都瞧在眼內,心中極是納罕,忽問道:“張丹楓果是張宗周的兒子麽?”雲蕾道:“是的。”張風府道:“那就真是出于污泥而不染了。看他所作所為,實是一個愛國的男兒,可笑千裏兄樣樣都好,就是對張丹楓卻固執成見,切齒恨他。”雲蕾心中一痛,說不出話。張風府忽又問道:“你也是從蒙古來的嗎?”雲蕾道:“我小時候在蒙古住過。”張風府道:“那麽與千裏兄的身世可差不多,你可知這次來的番王與澹臺滅明是什麽樣的人麽?”雲蕾道:“我未滿七歲,就離開蒙古,蒙古的事情,知得甚少,大人為何特別問這二人?”
張風府道:“朝廷近日有一件議論未定之事,甚是令人奇怪。”雲蕾想起自己乃是平民不便打聽朝廷之事,并不追問。張風府卻視她如同知己,并不顧慮,往下說道:“這番王名叫阿刺,在瓦刺國受封為‘知院’,即是‘執政’之意,權勢在諸王之上,而在太師也先之下。這次來朝,與我國談和,提出了三個條件:一是割雁門關外百裏之地,兩國以雁門關為界。二是以中國的鐵器交換蒙古的良馬。三是請以公主下嫁瓦刺王脫脫不花的兒子。閣老于謙力争不能接受此三條和約,說是中國之地,寸土不能割讓,鐵器讓與瓦刺,他的兵備更強,更是養虎贻患,萬不能允。至于以公主和親雖是皇室內部的事情,但有傷‘天朝’體面,亦是不允為宜。”雲蕾道:“于謙是個正直的大臣,公忠為國,有何奇怪?”張風府道:“于謙力主拒和,那自然毫不奇怪。奇的是奸宦王振也不主和。王振暗中與瓦刺勾通,我等亦有所聞。雁門關外百裏之地乃是金刀周健的勢和所在,朝廷管轄不到,王振恨極周健,十年來屢有密令交與雁門關的守将,準他與瓦刺聯兵,撲滅周健。我們都以為他這次樂得做個‘順水人情’,将雁門關外之地割與瓦刺了,誰知他也不允。再說到以中國鐵器交換蒙古名馬之事,十餘年來,王振就在暗中做這買賣。”雲蕾道:“也許是他內疚神明不敢公然資敵。”張風府笑道:“王振此人挾天子以令百官,又在朝中遍植黨羽,他有什麽事情不敢做,連皇帝也得看他顏色。再說當今皇上,甚是怕事,若然王振也主和的話,這和約早已簽了。”雲蕾道:“朝廷之事非我所知,我也想不出其中道理。”張風府道:“還有更奇怪的呢。王振非但也不主和,而且竟主張将這次蒙古的來使扣下,倒是于謙不肯贊成。王振素來暗助瓦刺,這次竟會有此主張,朝廷百官,無一人不覺奇怪。”雲蕾想起自己爺爺出使瓦刺,被扣留下來,在冰天雪地牧馬二十年之事,不禁憤然說道:“兩國相争,不斬來使,本來就不該扣留。”張風府道:“這事理我也明白,不過扣留使者之說,出于王振口中,總是令人大惑不解。”
坐談多時天色已暮,張風府命家人備飯,并對雲蕾說道:“雲相公在什麽地方住,不嫌蝸居的話,請搬到舍下如何?”雲蕾想起自己乃是女子,諸多不便,急忙推辭。張風府心道:“此人怎的毫不爽快,倒像一個未出嫁的閨中少女,遠不及張丹楓的豪放快人。”晚飯之時,雲蕾問起于謙的地址,張風府笑道:“你想見于大人麽?他這幾日忙于國事,就是他肯見你恐怕門房也不肯放你進去。”但到底還是把于謙的地址說了。晚飯過後,雲蕾堅決告辭,張風府挽留不住,送她出門,又提起張丹楓,笑道:“若然你那位朋友也到京都,等千裏兄中了武狀元,我一定要做個魯仲連,替他擺酒與千裏兄談和。你自然也要來作個陪客。”
雲蕾尴尬一笑,道:“張大人古道熱腸,我先多謝你這席酒。”辭別了張風府,獨自回到客店。
這一夜,雲蕾輾轉反側,不能入睡,一會兒想起了哥哥,一會兒又想起了張丹楓。想起自己只有這麽一個哥哥,而今遠道來京,偏偏他又調到宮內去當侍衛,雖說等他中了武狀元,可以相見,但事情到底涉茫,他中不了又怎麽相?中了之後,另生其他枝節又怎麽樣?不禁暗自嘆道:“我怎生如此命苦,連這世上唯一的親人也見不着。”心中想起了“唯一的親人”這幾個字,不知怎的,忽然又想起張丹楓。張丹楓雖然不是她的親人,但雲蕾每次想起他的名字,不知怎的卻總有一種親切之感,耳中又想起張風府的話,不禁苦笑嘆道:“你哪裏知道我家與他仇深如海,想勸我兄長與他和解,這苦心只恐是白費了。”
想起了張丹楓,又聯想到于謙,雲蕾摸出張丹楓托她轉交于謙的信,對着信封上那幾個龍飛鳳舞的字,如見其人。雲蕾心道:“張丹楓初次入關,怎會認識于謙?卻寫信介紹我去見他?”但想起張丹楓為人雖然狂放,做事卻甚缜密,從來不出差錯,也從來不說謊話,他既然能寫這封信,其中必有道理。又想道:“反正我也沒有別的門路去見于謙,不如就拿這封信去試試。嗯,門房若不放我進去又怎麽樣?難道也像在張家一樣,硬闖進去麽?于謙是一品大臣,海內欽仰的閣老,這可不能胡來呀。呀,有了,反正我有一身輕身的本事,就晚上悄悄去見他吧。”
第二日雲蕾養好精神,晚上三更時分,換上夜行衣服,悄悄溜出客店,按址尋到于家。在雲蕾想象之中,于謙乃是一品大臣,住宅必是崇樓高閣,堂皇富麗,哪知竟是一個平常的四合院子,只是後面有一個小小的花園,要不然就與一般小康之家的住宅毫無兩樣。
雲蕾心中嘆道:“到底是一代名臣,只看住處,就可想見他的為人了。”當下輕輕一躍,飛上瓦面,幾間平房,一目了然。只見靠着花園的那間房子,三面都糊着紗窗,窗棂縱橫交錯,分成大小格式的花紋,每一格都有一方小玻璃鑲嵌着,顯得甚為雅致,玻璃內燈光流映生輝,案頭所供養的梅花,疏影橫斜,也貼在玻璃窗上。雲蕾心道:“雅麗絕俗,真不像是富貴人家,這間房子一定是于謙的書房了。房中還有燈火,想他未曾睡覺。”放輕腳步,走近書房,忽聽得房中有談話之聲。雲蕾一聽之下,心頭有如鹿撞,這竟是張丹楓的聲音。這該不是夢境吧?他怎麽突然又來到這兒?雲蕾昨晚還夢見他,而今聽到他的聲音了,卻又不想見他。可是真的不想見他嗎?不,她又是多麽渴想見他一面啊,只是這麽偷偷瞧他一眼也好。
雲蕾輕輕走近,偷偷一瞧,紗窗上映出兩個人影,其中之一果然是張丹楓!正是:
碧紗窗上燈兒映,猶恐相逢是夢中。
欲知後事如何?請看下回分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