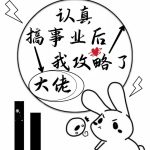萍蹤俠影錄第 15 章 (1)
更新時間:2007-1-12 23:23:20 本章字數:12797
門外馬嘶,漸遠漸寂,張丹楓不見了,但願張丹楓從此永遠不見了,但願人世間從來沒有過這麽一個張丹楓!多麽古怪的念頭,有血有肉的張丹楓,在密室中和自己作伴三日的張丹綱怎麽會從來沒有呢?是的,張丹楓走遠了,張丹楓不見了,可是他真的不見了麽?不,不!你看啊,他又來了,來了,來了!他的影子輕輕地,慢慢地,潛入了雲蕾的心頭,這一瞬間羊皮血書的陰影也給他的影子遮沒了。
雲蕾一片迷茫,是恨?是愛?是喜?是哀?都無從分辨,恩仇交織,愛恨難明,剪不斷,理還亂。霎那之間,一切思潮突然退滅,雲蕾腦中空蕩蕩的,似乎什麽也不曾想,什麽也不存在,迷茫中忽又似見張丹楓冉冉而來,在她耳邊低語:“小兄弟,小兄弟……”呀!那像爺爺一樣嚴厲,又像媽媽一樣慈愛的眼光!世界上有什麽人用這溫柔的聲音叫喚過自己?有什麽人用這樣的眼光注視過自己?除了這個自己但願他永不存在的張丹楓!
雲蕾的眼光緩緩移動,瞥見了玉幾上張丹楓留下的銀瓶,瓶中是張丹楓留給她的靈藥,“這是仇人的東西,不,不,我不能吃。……這是張丹楓最後的一番好意,不,不,我不應拒絕于他……”兩種念頭在雲蕾心中交戰,迷茫中忽又似見張丹楓含情脈脈地凝視着自己,在耳邊低聲說道:“小兄弟,你的傷雖已治愈,元氣尚未恢複,吃吧,吃吧……”那不可抗拒的眼光,那不可抗拒的聲音,雲蕾不知不覺地拿起了銀瓶,将三粒紅色的藥丸傾倒手心,納入口中。
也不知在地上坐了多久,只見敞開的墓門外日影西移,想已是黃昏時分,忽聽得外面一聲馬嘶,雲蕾心頭一震,跳了起來,想道:“難道是他又回來了?”
只聽得一聲歡呼,但見周山民疾奔而來,高聲叫道:“雲妹妹,你果然還在這裏!哎喲,你中了那□的毒手嗎?”雲蕾淡淡一笑,搖了搖頭。周山民挨在她身邊坐下,朝她的面上看了又看,憔悴的顏容,失魂落魄的模樣,令他無限擔心。
雲蕾定了定神,只聽得周山民道:“原來你和他躲在這個墓中,你沒有吃他的虧吧?你知道他是誰?他是大奸賊張宗周的兒子,是你爺爺的大仇人!”周山民此言一出,以為雲蕾必然吓得跳起,豈料雲蕾只是低低地應了一聲,說道:“嗯,我知道了。”這一下,反而把周山民吓得跳了起來,大聲叫道:“什麽?你知道了?你什麽時候知道的?”雲蕾身子不動,低聲說道:“我剛剛知道的,澹臺滅明方才來過……”周山民噓了口氣,道:“原來如此,我道你若早知他是仇人,怎會與他作伴?你和他動了手了?可真的沒受傷麽?”
雲蕾道:“我受了白摩诃的毒手所傷,是他給我治的。”周山民道:“他?他是誰?”雲蕾道:“我爺爺的大仇人!”周山民一怔,道:“他不知道你是雲靖的孫女兒?”雲蕾道:“我用劍刺他,他知道了!”周山民又是一怔,忽似頓然醒悟道:“哦,我知道了。這奸賊初時不知你是他仇人,這才将你籠絡,想把你收為己用。後來你拔劍刺他,他不是你的對手,所以逃了。可惜你受傷剛好,氣力大約還未恢複,要不然定可一劍将他刺死,我也不用費這麽大的勁了。”
雲蕾低首不語任由周山民猜度。只聽得周山民得意笑道:“早知他武功如此稀松平常,我也不用費這麽大的勁,求那轟天雷石英共同傳下綠林箭了!”雲蕾吃了一驚,道:“什麽,綠林箭?”
周山民笑道:“你江湖閱歷尚淺,還不知道什麽是綠林箭嗎?綠林箭是綠林領袖傳下的令箭,綠林英雄,見了令箭,赴湯蹈火,亦不敢辭。雲妹妹,真是神差鬼使,張宗周的兒子居然敢一個人闖進關來,你的大仇是定能報了!”
羊皮血書的陰影又在心頭擴大起來,雲蕾對這消息也不知道是喜是悲,爺爺的遺囑那是萬萬不能違背,張家的人一個也不能饒,那麽就讓他給別人殺了,免得自己動手。可是一想到張丹楓要被綠林群雄亂刀斬死,那景象卻是想也不敢一想。只聽周山民又在旁邊說道:“雲妹妹,自你離山之後,我十分挂念。”聲音很是溫柔,雲蕾擡起了頭,有氣沒力地道:“嗯,多謝你的記挂。”周山民見她這副沒精打彩的樣子甚是失望,仍往下說道:“我總想再見着你,可是山寨事忙,哪裏能夠?上月我們在邊境的探子,探出張宗周的兒子一個人闖進關來,扮成一個秀才模樣,騎着一匹白馬,極是神駿。我爹和山寨中人商量,大家都說,張宗周的兒子闖進關來還能安什麽好心,一定是打圖謀中國的壞主意了。我爹就叫我追蹤,會同各地的綠林領袖,共傳綠林箭定要将他擒獲。此地是山西境內,晉、陝兩省的武林盟主,乃是石英,偏偏我去尋他之時,他已不在黑石莊中。後來見了石英的女兒,才知道原來你竟然做了石英的女婿。石小姐可還是真的喜歡你!”
雲蕾微微一笑,道:“你看石小姐她如何?”周山民道:“武藝也還過得去。”雲蕾道:“其他呢?”周山民道:“我與她相識還不到半天,怎知什麽‘其他’?”雲蕾又是微微一笑。本想再說,可是心中懸挂“綠林箭”之事,納悶石英對張丹楓那麽尊敬,又何以會與周山民共傳下綠林箭?此一疑問,急欲分曉,便不再打貧,讓他說下去。
周山民往下說道:“那日我與石姑娘追趕澹臺滅明的徒弟他的馬是大宛良馬,追出了三五十裏,我們的馬都累了,他的馬還是奔走如風,追不上啦!”雲蕾插口道:“石姑娘呢?”周山民一笑說道:“你這位夫人對我似是甚有成見,一路和我擡杠,聽她言下之意,似乎甚不滿意我是你的義兄,倒把我弄得莫名其妙,我是你的義兄,又幹她什麽來了?”雲蕾心中好笑,想不到那晚“洞房之夜”,與石翠鳳屢屢提及義兄,反而弄巧成拙。
周山民做了個受委屈的表情,聳肩說道:“追不上敵人,她和我吵了一架,說要獨自回家,也不願帶我去見她的父親,還吵着要我把那枝珊瑚還她,她像那珊瑚是她命根子似的。”雲蕾不覺又是抿嘴一笑。周山民道:“我知道那珊瑚是你給她的聘禮,她對你真情一片,怪不得寶貝如斯!”雲蕾笑着道:“這回是你給她的聘禮,不是我給的了。”周山民面上一紅,道:“你這小鬼頭,亂嚼舌頭,看我撕你的嘴。”雲蕾一笑避開,道:“說正經的,石姑娘既不願帶你去見她的父親,你的綠林箭又從哪裏得來?”
周山民道:“無巧不巧,石姑娘去後不久,我策馬西行,不久就遇見了轟天雷石英,他還不知道他女兒曾和我一道呢。想來是他父女各走一途,所以沒有見面。”雲蕾道:“石英是不是和四個珠寶商人一道?”周山民道:“是呀,他行色匆匆好像有什麽急事,無暇與我多說。我問他要綠林箭,正想一一詳告于他,他卻搖手說道:‘金刀寨主的俠義威名,天下誰人不知!既是你們要追捕的,那就必定是萬惡不赦之人,不必說了,綠林箭拿去便是!我有急事,恕不陪了。少寨主,你事情了結之後,那時請再到黑石莊一敘,詳細談談。’他問也不問便把綠林箭交給了我,立刻與那四個珠寶商人走了。”雲蕾心道:“原來如此,若然石英多問一聲,知道所要追捕的是誰,那就絕不至于有此誤會。”
周山民續道:“我和石英在孟良崗附近會面,那附近便是藍天石寨主的地頭,我将綠林箭交給了他,叫他三日之內,遍傳綠林同道。我在他寨中住了一天聽候消息,事情順利得很,有石英和我爹爹聯名,好幾個從來不肯聽人調遣,雄霸一方的綠林大豪,都願意拔刀相助了。雲妹妹,這次你家的大仇一定能報了!哎,怎麽?你怎麽還不歡喜呢?”雲蕾面色蒼白,聽他一問,強笑說道:“嗯,我有點不大舒服,現在好了。我、我很高興!”
周山民道:“綠林箭有綠林同道一手傳給一手,不必我再多管。我想起那日在此遇見你的紅鬃戰馬,便再回來找你,天可憐見,果然見着你了。”雲蕾不言不語,周山民正想再吐衷曲,忽而好似聽見什麽似的,急急伏在地上。
雲蕾問道:“是不是又有什麽人來了?怎麽我聽不見?”周山民站起來道:“來人還在七八裏外。”從容地把外面石門掩上。這“伏地聽聲”的本領,是綠林高手的絕技,亦是經驗累積所成,雲蕾雖然學過,火候卻還差得太遠。
周山民看了雲蕾一眼,微微笑道:“你該換衣服了吧?”雲蕾自那日向張丹楓露出本相之後,便換了女兒服飾,這時被周山民提醒,不覺粉面飛霞,低頭走進密室,把門關上。周山民一人留在門外,心中甚是狐疑:看雲蕾這個樣子,莫非在她未識破仇人面目之前,竟已到了和他熟落無拘的地步?
雲蕾在密室裏打開行囊,腦海中不覺又泛出張丹楓似笑非笑的樣子,“小兄弟,小兄弟……”那令人心魂動蕩的聲音,又似在耳邊響了起來。雲蕾随手取出幾件女裝衣裳,狠狠地一件一件撕成兩半。她恨什麽?恨這些衣裳嗎?不,她自己也不知道恨的是什麽,只是心中的抑郁卻好似随着這裂帛之聲而消散空溟,又好似撕毀了這些衣裳,就等如撕毀了自己的記憶。她真願意自己真是一個男兒,如果是一個男兒的話,也許會少了許多苦惱。
雲蕾一件一件地撕下去,突然停下手來。她手上提起的是一件紫色的羅衣,記得露了女兒本相之後,第一晚換的就是這件衣裳,記得那時張丹楓露出異樣的目光,啧啧地稱贊自己的美麗。雲蕾嘆了口氣,把羅衣一展,瞧了又瞧,這是張丹楓贊賞過的衣裳啊!她輕輕地撫摸那柔軟的絲綢,又輕輕地把衣裳折了起來,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好,不再撕下去了。
密室外傳來了周山民踱來踱去的腳步聲,雲蕾猛然醒道:“我在這裏發傻,周大哥可等得不耐煩了!”随手翻出一件男裝衣裳,匆匆換上,走出門來,只見周山民倚在外邊的石門說道:“你聽那馬蹄之聲,來人已在一裏之內。到這荒郊墓地來的,必定不是尋常之人,你精神如何,能用劍嗎?”
雲蕾道:“還可對付。周大哥,你再給我說說綠林箭之事吧。”周山民想不到她在這個時候還會和他閑聊,詫道:“綠林箭這時想已傳各地,還有什麽可說的呢?”雲蕾道:“這山西一省,有哪些厲害的綠林英雄?”周山民笑道:“哦,你是擔心報不了仇嗎?山西省的綠林高手可多着呢!啊,我還忘了告訴你一事,你的二師伯潮音大師新近從蒙古歸來正在此地,只怕他也知道我們傳綠林箭之事了。”雲蕾奇道:“是嗎?他幾時到了蒙古?你碰見他嗎?”周山民道:“我沒碰見,聽人說的。嗯,不要響,你聽,有人在外面叫你!”話聲一停,果然聽得有人在外面叫道:“雲蕾,雲蕾!”這正是石翠鳳的聲音,雲蕾怔了一怔,正想說道:“不要開門!”周山民卻已把她放了進來。
石翠鳳旋風一般地飛跑進來,一見雲蕾,喜出望外,歡聲叫道:“雲相公,你果然還在此地!”說着,說着,不覺滴下淚來,又哭又笑。周山民道:“雲相公傷勢風好,你不要嘈吵他了!”石翠鳳這才看到周山民也在旁邊,柳眉一豎,怒道:“我們夫妻之事,你管得着!”上前靠近雲蕾低聲問道:“雲相公,你着了黑白摩诃的毒手麽?”雲蕾道:“你不用擔心,現在已經全好了。”輕輕拉起石翠鳳的手,道:“周大哥說得不錯,我是想歇一會兒,你看,天色已經晚了。”石翠鳳面色漲紅,心中怒道:“你就幫着你義兄,全不把我放在心上。”可是雲蕾既然如此說法,她也不好發作出來。
周山民在旁邊噗嗤一笑,石翠鳳橫他一眼,道:“你笑什麽?”雲蕾插口道:“我肚子餓啦,石姑娘麻煩你給我弄飯,這裏有米,還有肉脯和臘羊腿。我暫時歇一歇,飯熟了你再叫我。”自顧自地走進密室,周山民也想跟着進去,剛剛走了兩步,石翠鳳忽然怒聲叫道:“喂,你來幫我倒水洗米!”周山民好不尴尬,只好退出,雲蕾向他微微一笑,好像小孩子做了一件惡作劇,甚為得意。
周山民悶聲不響地幫石翠鳳洗米、生火、弄飯,石翠鳳也悶聲不響,毫不理睬于他,顯然還在生氣。雲蕾在密室裏獨自思量,在想怎樣将他們撮合,聽外面兩人毫不交談不覺暗笑:不是冤家不聚頭,翠鳳如此恨他,想必是以為我偏向義兄,故此,對他心有芥蒂,若然她知道我和他同是一樣的女兒身份,豈不要啞然失笑?嘴裏咀嚼着“不是冤家不聚頭”這句說話,忽然想起自己與張丹楓初見之時,也是對他憎厭,又不覺輕輕嘆了口氣。
雲蕾胡思亂想,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,聽得石翠鳳敲門叫道:“雲相公,飯熟啦!”雲蕾這才如夢初醒,開門出來,一眼瞥見石翠鳳和周山民互不理睬的尴尬模樣,不覺又失聲笑了出來。
石翠鳳和周山民都搶着替雲蕾盛飯,石翠鳳又橫了周山民一眼,雲蕾微微一笑,接過了石翠鳳遞來的飯碗,周山民想起自己太過着跡,心怕雲蕾見笑,面上又是一紅。雲蕾道:“翠鳳,我這位周大哥乃是日月雙旗金刀少寨主,見多識廣,又是極好的好人,你該多向他請教。”石翠鳳“哼”了一聲,道:“我知道。你的義兄自然是個了不得的英雄豪傑,要不然你怎會那樣聽他的說話!”
周山民尴尬苦笑,雲蕾解開僵局,笑問石翠鳳道:“周大哥說,你那天趕着回家,怎麽又出來了?”石翠鳳道:“我回到家後,不多一會,爹爹也回來了。他面色非常沉重,好似有什麽極大的心事一般。我問他見着你沒有,他說沒有見着,但已确實知道你還在黑白摩诃的古墓之中,不過有人不許他見到你。我聽了非常奇怪。”
周山民也覺十分奇怪,忍不住插口說道:“你爹爹武功超卓,威震綠林,誰敢攔阻?”石翠鳳聽他稱贊自己父親,對他惡感稍減,卻仍是偏着頭對雲蕾道:“我再三問爹爹,那是誰人,爹爹總不肯說,只說他天不怕,地不怕,只是那人的說話不能不聽。又說那人說過我的婚事包在他和雲相公的身上,所以叫我不要心煩。”說至此處,石翠鳳兩頰飛紅,低頭弄衣,不敢和雲蕾的目光相接。雲蕾心中暗笑,又是歡喜又是悲哀。暗笑石翠鳳的那片女兒羞态;歡喜石英對張丹楓的尊崇;悲哀的卻是自己的遭遇。她已知道石英所說的那人乃是張丹楓,但卻不願明說出來。
石翠鳳接着說道:“這十多天來,我爹爹行事十分古怪,平日他有什麽事都和我說,這十多天來,卻事事都瞞着我,那白馬小賊的來歷,那張圖畫的來歷,以及攔阻他的人是誰,這種種怪事,都不肯向我透露半點。我生氣他也不理,卻要我立刻替他送信。”雲蕾奇道:“送信,送與誰人?”石翠鳳微微一笑,道:“送給一個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奇人,這時不先說與你知,你若願意見那奇人,明日與我同去。”周山民道:“山西省內有什麽大名鼎鼎的奇人?是藍大俠嗎?是郝莊主嗎?是……”石翠鳳“哼”了一聲,道:“別胡猜啦,你雖然是大名鼎鼎的金刀少寨主,也不見得能識遍江湖上的奇人。”周山民碰了一個釘子,悶聲不響,雲蕾笑道:“你們別盡擡杠啦。這麽說,明天我與周大哥都跟你去。時候不早,我要睡啦。”推開小門,走進密室。
石翠鳳略一遲疑,也跟着走了進去,雲蕾柔聲說道:“鳳姐姐,那邊還有一間房子。”石翠鳳又羞又氣,站定腳步,正想說話,只聽得周山民又叫道:“呀!這古墓裏面真是別有天地,有如地下宮殿一般,除了這個大廳,還有好幾間房子,真是太好啦。你們一人睡一間房子,我睡在大廳替你們守夜。賢弟,你傷勢初愈還要靜養,早些睡吧,不要勞神多說話了。”石翠鳳面紅直透耳根,霍地跳了出來,只見周山民似笑非笑的眼望着她,不再言語。石翠鳳恨不得一刀把他劈為兩段,氣呼呼地推開左邊小房的房門,好半夜還睡不着。
第二日一早,三人起來,雲蕾和周、石二人點頭說話,他們二人卻是互不理睬。三人弄了早飯,吃過之後正想出門,只聽得遠處一聲馬嘶,周山民跳起來道:“這馬來得好快!”話猶未了馬蹄之聲已是越來越近,又是兩聲長嘶,石翠鳳“咦”了一聲,說道:“好像是那匹白馬的叫聲!”雲蕾面色蒼白,搖搖欲倒,周山民拔刀叫道:“好,他倒先尋我們來了,合力鬥他!”雲蕾伸手拔劍,手指顫抖,寶劍還未出鞘只聽得“轟隆”巨響石門已給來人撞開,沙石飛揚,一匹白馬飛奔而入!
只聽得周山民叫了一聲,搶着上前施禮,雲蕾定睛一望,那馬上的騎客卻不是自己意料之中的張丹楓,而是出乎自己意料之外的潮音和尚,一種突如其來的歡喜與失望交織心頭,令得雲蕾怔怔地站在潮音面前,霎那之間,說不出話。潮音和尚見了女扮男裝的雲蕾,也是一怔,“咦”的一聲,正想問話,周山民急忙一扯潮音和尚的僧袍,将他拉過一邊,低聲說了幾句,潮音和尚猛然哈哈大笑,向雲蕾招手說道:“蕾兒,你過來,待我仔細看看,幾年不見你已經長大成人啦!”雲蕾叫了一聲“師伯”,上前施禮,石翠鳳也随在雲蕾後面上前谒見,潮音和尚雙眼一翻,向石翠鳳掃了一眼,忽而縱聲笑道:“好俊的娘兒!蕾兒,你可不能虧待于她。”石翠鳳裣衽問好,潮音忽又笑道:“人長得怪俊,不知你可會弄飯菜?”石翠鳳一愕,周山民接口說道:“弟嫂聰明極啦,豈止會弄飯,還燒得一手好小菜。”潮音和尚笑道:“好極,好極!我兩日之間,走了七八百裏,肚子餓極啦,快給我去燒菜弄飯!”石翠鳳愕然想道:“你肚子餓也不該如此無禮,我爹爹都從沒用過這種口氣向我吩咐。”潮音和尚把馬系好,大馬金刀的坐了下來,又催促道:“山民賢侄,你也去幫幫我的侄婦弄飯,放三斤米菜不要太多,有六七樣便成!”潮音和尚毫不客氣的差遣,把石翠鳳弄得哭笑不得,心道:“怎麽雲蕾的義兄、師伯,全都是這樣不近人情的怪物!”礙着雲蕾情面,只好撅着嘴兒到裏面弄飯。
周山民亦步亦趨地也跟了進來,石翠鳳氣惱之極,勃然發作,怒聲說道:“不要你來幫我。”周山民笑道:“噓,小聲點。你不知道雲蕾的師伯是個出名的莽和尚嗎?你若和我在這裏吵架,叫他知道,一定會在雲蕾面前說你。”石翠鳳果然不敢大聲,板着臉兒,瞅了周山民一眼。周山民又笑道:“再說那和尚胃口真大,七樣菜還說不多,你一個人弄得了嗎?”石翠鳳一想果是道理,只是氣恨不過,張頭出去,對着潮音和尚的背影狠狠地啐了一口。周山民又噓了一聲道:“他們師侄在那裏說話,你不要打擾他們。這個莽和尚脾氣當真不好,你可要小心。”石翠鳳氣得幾乎要哭出聲來,怒道:“好呀,你們師侄兄弟,就我一個是‘外人’,我去問雲蕾去!”外面潮音和尚猛然咳了一聲,石翠鳳說說而已,可還不敢真的發作,只好與周山民一道燒菜弄飯。
周山民心中暗笑,他是故意做好做壞,好讓潮音和尚與雲蕾一道放心說話。殊不知雲蕾卻也是別有心思,好讓周山民多和石翠鳳一起。周、石二人進入裏面弄飯之際,她便将在黑石莊入贅之事,細說與師伯知道,把潮音和尚弄得笑個不停。笑完之後,忽然正色說道:“你倒開心,我可為你在蒙古氣得死去活來!”
雲蕾吃了一驚,只聽得潮音和尚問道:“蕾兒,你還記得你是哪一年和爺爺回到中國的嗎?”雲蕾道:“記得,那是正統三年。”潮音道:“今年呢?”雲蕾道:“今年是正統十三年。”潮音和尚嘆了口氣道:“好快啊,眨一眨眼便是整整十年。十年之前,我和你的三師伯謝天華在雁門關外擊掌立誓,一個撫孤,一個報仇。我負責将你帶回小寒山交給四妹撫養,他負責遠赴蒙古,将奸賊張宗周刺殺,為你複仇。這事情你師父想必早已對你說了?”
雲蕾目有淚光,答道:“早已說了,多謝師伯們為**心了。”潮音和尚又嘆口氣道:“你多謝得太早了。”頓了一頓往下說道:“我與天華師弟以十年為期,約定今年在雁門關外一個地方相見。不料到期他卻不來,道路傳言說他生死莫蔔,還有人說,他已被張宗周擒了,于是我遂匹馬單騎遠赴胡邊,深入瓦刺。天華弟如有不測,這報仇的事兒只好由我擔承。”
雲蕾插口說道:“我師父說謝師伯武功卓絕,智勇雙全,想來該不至于遭人毒手?”潮音和尚冷冷一笑,說道:“謝天華确是武功卓絕,要不然我已替你報了仇了。”雲蕾愕然道:“二師伯此話,令人難解。”潮音和尚拍的一掌,将玉幾砍掉一角,大聲說道:“我也是十分不解呀!”又是一聲長嘆,往下說道:“我潛入瓦刺,暗中打聽多時,總打聽不出天華師弟的下落,想要複仇,那張宗周有澹臺滅明保護門禁又極森嚴,焉能輕易下手?我在瓦刺度日如年,心焦極了。不意,到了上一個月,卻忽聽到一個消息,說是澹臺滅明已不在張宗周的左右,大約是給那奸賊差遣到什麽地方辦事去了。我打聽屬實,于是選擇了一晚月黑風高的晚上,單身闖入張賊的丞相府。”
“那張賊的丞相府好大,他也真會享受,竟在漠北苦寒之地,建起像江南一帶的園林,相府中的房屋,也都是蘇杭兩地的樓臺亭閣格式。我摸了半夜,捉到了一個小□,才打探出張賊住在花園東角的一座樓中。”
“這時已是五更時分,可怪得很,張賊竟然還未睡覺,獨自坐在房中寫字,低首揮毫,絲毫沒有注意到窗外有人要取他的性命。我掌心早已扣了三枚金錢镖,一看機不可失,立刻用連珠手法,取他‘将臺’、‘璇玑’、‘金泉’三道大穴。我的錢镖在三丈之內,百發百中,莫說他在凝神寫字,即算武藝高強之輩,有所防備,也難以一一躲開。”
“不料錢镖一發,只聽得叮,叮,叮,連聲疾響,三枚錢镖都在他的眼前落下。那房中有複壁暗門,張賊身一靠牆,立刻躲了進去,我跳進去一抓,只抓緊他的一幅衣角,就在其時有人突然跳出一掌将我推得仆倒桌上,蕾兒你猜那人是誰?”
雲蕾沖口說道:“莫非是澹臺滅明沒有外出故作圈套?”說了之後,猛然想起上月月初,自己在雁門關外,還曾和金刀周健合戰過澹臺滅明,甚是懷疑,接着說道:“可是澹臺滅明怎能有分身之術?但若非澹臺滅明又有誰有那麽高的武藝?”
潮音和尚冷冷一笑,大聲說道:“若是澹臺滅明,那倒毫不足怪,這人卻是與我情如手足的同門兄弟謝天華!”雲蕾驚道:“是三師伯?”潮音道:“不錯,是謝天華!這才把我氣得死去活來。我喝問他道:‘十年之約,你忘記了嗎?你是複仇還是事仇?’他瞪我一眼,刷刷刷,一連三劍,将我逼出屋外,緊緊跟蹤追出。在同門之中,他的武功最強,我明知不是他的對手,可是這時恨極氣極,反轉身來,便要和他拼命!”
“可怪他在屋內那樣狠心,在屋外卻并不動手,避我數招卻忽地低聲說道:‘你知道張宗周是什麽人?’我怒極罵道:‘憑你如何說法,總不能把張賊說成好人!’劈面又是一刀,輕身夜行,不便攜帶禪杖,我帶的乃是短刀,使來甚不趁手,哪能斫得他着?只斫了兩刀,猛聽得他低說了聲:‘好糊塗的師兄!’忽地欺身直進,一伸手就點了我的軟麻穴,将我背了起來。這時相府內已是人聲鼎沸,守夜的武士都已驚起,他背着我竄高縱低,轉彎繞角,轉瞬之間,便到了園中一個靜僻的角落,那裏有一個精致的馬廄,他從馬廄中牽出一匹白馬,解開我的穴道,低聲說道:‘多年兄弟難道你還不知我的為人?快走,快走!’我不肯上馬,對他說道:‘你若不與我說個明白,我決不走!’他面色一變,忽然厲聲說道:‘你若不走,休怪我手下無情,不但要走出相府,我限你三日之內,離開蒙古,否則取你性命!’我大怒揮刀再斬,刀卻給他搶去折斷,一下子将我抛上馬背,喝道:‘你真的不想要命了麽?’我絕料想不到他如此反面無情,自思:他既如此棄信背義,我白送了性命,有誰知道他是本門叛徒?不如權且避開,以後再找他算帳。那匹白馬神駿非凡,不聽人騎,幸而我還有點功夫,強力将它制服,騎馬沖出相府,背後數十百騎,紛紛追來,聲勢洶洶,只聽得那些人都在喝罵:‘好大膽的賊人,居然敢偷了丞相的寶馬!’哈,原來這白馬竟然是張賊的坐騎,怪不得如此神駿,它被我制服之後,放開四蹄疾跑,真如追雲逐電一般不消多久,便把那些人都撇在後面,再也追趕不上。那一晚我雖然被氣得死去活來,卻也意外地得了一匹寶馬”那匹白馬就系在廳中,似乎知道潮音和尚說它,又嘶了一聲。雲蕾細看,這匹白馬和張丹楓那匹“照夜獅子馬”甚是相像,只是頸上多了一撮黃色的鬃毛,想來都是同一馬種。
潮音和尚道:“蕾兒,你在出神想些什麽?”雲蕾說道:“三師伯若是甘心事仇,又焉肯将張宗周的寶馬也送給你?”潮音道:“所以我是十分不解呀!若非這匹寶馬,我也逃不出蒙古。”雲蕾搖頭道:“此事實是費人猜疑!那張宗周是什麽人?難道--”潮音“啪”的一掌,又将玉幾打掉一角怒道:“那張宗周是奸賊世家,歷代在瓦刺為官,助瓦刺整軍經武,圖謀吞并中華,這樣一個天下皆知的大奸賊,你說他還能是好人嗎?”雲蕾想起爺爺被折磨,在冰天雪裏牧馬二十年之事,心痛如割,顫聲說道:“他是萬惡不赦的奸人,是我家的大仇人!但,你看他是不是另有來歷?”潮音眼珠一轉,忽然似想起什麽事情似的,從袋中掏出一個紙團,展開說道:“那晚我行刺張賊,一擊不中,被天華一掌将我推開,恰巧仆倒在張賊的書案上,我随手一抓,拾起了這個紙團,就是那晚張賊所寫的。我想那奸賊深夜不眠,所寫的可能是什麽機密文書,就把它帶回來了。可恨他寫得那麽潦草,我鬥大的字雖還認得幾個就認不出這龜兒子寫的是什麽東西。你給我看看,每一行都是七個字,不多不少,一共只有二十八個字,莫非不是什麽文書是什麽詩呀詞呀之類的玩意嗎?”雲蕾忍俊不禁,噗嗤一笑,将那張紙接了過來,細細一看,沉吟不語。潮音問道:“這龜兒子寫的是什麽?”雲蕾道:“是一首詩。”念道:“誰把蘇杭曲子讴?荷花十裏桂三秋。哪知卉木無情物,牽動長江萬古愁!”也正是張丹楓展圖感慨,曾經對雲蕾吟過的那首詩。
潮音眉頭一皺,道:“那奸賊深夜不眠,寫的就是這麽樣的一首詩嗎?什麽愁不愁的,長江怎麽會愁呢?哼,不通,不通!”雲蕾忍不着又是噗嗤一笑,道:“這是宋朝一個名詩人的詩,長江自古以來是南北交戰的戰場,我看這首詩感慨很深呢。”潮音尴尬笑道:“那麽就算是我這老粗不通,你給我說他寫這首詩是什麽意思?”雲蕾沉吟半晌,忽道:“這本是宋朝謝處厚寫的一首詩,但頭一句和尾一句都給張宗周改了一個字。原詩頭一句是:‘誰把杭州曲子讴?’給他改成‘蘇杭’了,末一句是将‘地域之愁’改為‘時間之愁’,那是傷心人別有懷抱,不必去理會它。末一句本是‘萬裏愁